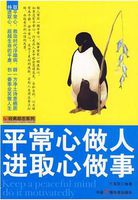他们给我做了核磁共振扫描,最终把我送到了普通病房。我浑身剧痛,不断地呻吟着,吗啡也无法减轻这种疼痛。护士进来说我要是再叫,他们就把我赶出医院。这真是有趣,他们要干嘛?把我的床扔到停车场,把我丢下?还是把我的床扔到汽车站,让我乘一辆公交车回家去?再说,我的家也没了。我忍不住发出呻吟,痛彻心扉,肝肠寸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痛。
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清醒的时候,就盼着警察来听听我的故事。但没有人来,而且似乎我无法让别人相信我的故事。我知道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一定对我很好奇。我可不像玫瑰那样闻起来香喷喷的,头发也油乎乎地黏在一起贴在头皮上。换句话说,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许多流浪汉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而我看起来正像是这样。
第二天,我姐姐米歇尔和弟弟艾利克斯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弟弟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哪,你是从搅拌机里爬出来的吗?”
我根本不需要镜子,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是的,我看起来一定无比凄惨。姐姐说我看起来像一只浣熊,还问我眼睛怎么搞成这样。我很高兴他们来了,让我不再孤单,但我仍然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脆弱。绑匪本来是要我死的,但我却活下来了。那些恶棍一旦发现,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要我的命。姐姐跟吉恩·罗森谈了谈,他们告知医护人员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与我有关的信息。院方保证尊重我们的意愿,但是他们并未信守承诺。
起初几天,我只能忍受疼痛,什么都干不了。几天以后,我开始打电话注销信用卡。他们所享受的空前的疯狂购物热情震惊了我,他们花了16万多美元。我试着跟信用卡公司解释情况,但事实证明这非常难,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不可能的,没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打电话给熟食店经理弗雷迪,让他把店里的锁换了,以免他们把剩下的东西也卷走。我努力挽救着我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已经所剩无几。我的指示弗雷迪还是可以执行的,他来到医院告诉我除了我的电脑,其他东西都在。至少他们没来得及把熟食店洗劫一空。
我打电话给银行,惊喜地发现我的一个账户里还有4万美元的余额,显然这笔钱还留在账户里是因为我的签名不过关。令我无法理解的是,银行既然能对一张4万美元的支票提出质疑,为何却轻易地兑现了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我冻结了账户,没有解释原因,这个时候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我的。我知道如果绑架我的人还没有发现我活下来了,那么我现在冻结账户内剩余的资产就会提醒他们我还活着。我查询了佣金和共同基金账户,但为时已晚,这些钱都被洗劫一空,甚至连我的个人退休账户也难逃一劫。
当别人发现你处于低谷、无比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办法占你的便宜,这着实让我感到心寒。弗雷迪到医院里看望了我,但他并没有换掉熟食店的锁。他拿着熟食店的信用卡去买私人物品了,总共花了有一千美元。多好的一个人啊,真是谢谢你了。连他都堕落到如此境地,真是太让我震惊了,但转念一想,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呢。
随着身体开始痊愈,我逐渐陷入一种恐慌,姐姐也是同样的心神不宁。她的直觉告诉她得尽快带我出院。我姐姐性格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她行事绝不拖泥带水,思路很清晰。如果离开医院,我能去哪儿呢?我没有了家,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的身体状况更不能去哥伦比亚。一个月之前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一份生计,现在都没了。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形也令她心里惴惴不安。她的直觉是对的,弟弟也是精神高度紧张,进病房的时候还带着一根“安全”手杖,也就是一根小型警棍。我们的性命其实朝不保夕,那帮暴徒随时都会端着枪破门而入一通扫射。
我们反复思量,考虑在我住院期间,雇一个贴身的私家侦探。我们给吉恩·罗森打电话,他推荐了一个叫做艾德·杜波依斯的人。我们给杜波依斯打了电话,不过对于他听了我故事之后会作何反应依旧心里没底。然而,他来到医院,见了我之后,就相信了我。他告诉我们雇人24小时贴身保卫的价钱,这价格令人望而却步,我们立马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艾德建议我们出城,留在迈阿密很危险。在接下来经历的一连串考验中,艾德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在商讨其它办法的时候,米歇尔跟医护人员去拿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他们把我的靴子和一套撕烂了的内衣给了她,这就是我剩余的所有东西。如果穿这一身,我就得光着身体只穿一双靴子走出医院了。
姐姐决定带我乘飞机转往纽约她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那样她就能照看我。医生来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她把她的决定告诉了他。
医生表示反对,对她说我的身体情况哪儿都不适合去,他不会同意的,也不会签出院单的。姐姐这时尽显强人本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她不在乎他怎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周五她就带我去纽约,并且还会让我一切准备就绪。医生肯定从没遇到过这么直白地跟他讲话的人,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我告诉他我没有经历什么车祸,那是一场蓄意的谋杀,还解释说我被绑架了,请他们报警。
姐姐和弟弟站在我身边,一起目睹医生面部表情的扭曲,他对刚刚听到话表现出震惊和难以置信。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永远印刻在我脑海中,只能说那令人感到很不真实。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诡异地笑了一下,就离开了房间。我们姐弟三人明白自己已经身处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必须马上撤离。
第二天,姐姐安排了一家当地的空中救护公司将我送往纽约。早上八点,我们就将离开这个天堂和这里所有美好的回忆。
周五早晨,我盼望着离开这个在过去一个月给我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地方。那天早上,我偶然听到两个医生在我的病房外谈话。在他们看来,整件事都非常奇怪。我来到医院时是个无名氏,也没有文件或是任何线索能表明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为什么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就不能费心去报个警吗?
后来,医生进来拿走了交叉缠绕在我身体上的导管。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似乎还在梦里,我很清楚,故事的第二章就要开始了。姐姐安排很周到,她找了一个护士陪着我们前往纽约。
我被抬到担架上,又被转移到一辆轮床上,最后被抬到了救护车上。到达机场时,我的轮床也上了飞机。我跟弟弟道了别,他不一同前往,而是回坦帕市2的家。姐姐也登了机,飞机的门关上了。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眼泪流出了我的眼眶。这既是悲伤的眼泪,也是喜悦的眼泪,既是因为上个月我所经历的磨难,也是因为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终于能前往一个更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人。
那天上午大概十点,卢戈、他的跟班、德尔加多以及另一个同伙来到了医院。他们疯狂地打电话想找到我,第一个电话就打往太平间,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期望在那儿打听我的消息。但结果让他们感到震惊,我并不在那儿。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活了下来。他们又给所有的地区医院都打了电话,最终在杰克逊纪念医院找到了我的踪迹,不知是谁大发慈悲,把我的房间号告诉了他们。还记得他们是怎么保证不会泄露任何消息的吗?
他们到医院来杀我,带了装有消声器的手枪,打算杀死任何跟我在一起的人和任何阻拦他们的人。他们的计划是用枕头闷死我,不留下任何闪失,走进我的房间后,没看到人,以为我去接受检查了。卢戈跟护士谎称是我的朋友,问我去哪儿了,护士告诉他我一早就走了。卢戈和他的同伙大惊失色,他们的猎物逃脱了。
***
1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
2佛罗里达半岛西安海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