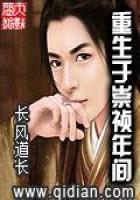李慕道觉得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做为相府的郎中,在别人都嫌弃他,不信任他的时候,相爷请他来看病。眼见着大人受那非常人可以忍受的罪,他心里万般过意不去。
做为鬼医的传人,他们治病一向只讲疗效,从不管病人受不受得了,所以他们制出的药还要比一般医生的药让病人更难以忍受些。但是也好的快得多。
可现在他根本就对大人的病束手无策,能做的就是给些止痛,安神的药,这些药在大人身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顶多一时半刻就过了药效,反而是喝起来苦得让人咂舌。
每次看大人深呼一口气,然后用管子一气把他制的苦汤子吸完,心中都万分愧疚。可大人不但没有指责过他,反而给他经费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甚至于不顾自己的病痛,谆谆教导他。这对受人点滴之恩都要涌泉相报的他,简直是一种折磨。
梅香儒似乎是看出了他的不自在,轻声叫他过来,问道:“先生,我背上的伤快好了吧,我想躺一会,再这么趴下去,肋骨会不会断裂?现在就痛的受不了。”李慕道赶紧收拾好心情,让小凤着大人脱了衣衫,仔细检视起伤口来。
上好了药,才松了口气,对大人说道:“伤口基本上已经愈合,大人若是想躺,那就躺着吧,伤口已经无碍了。”
梅香儒哂笑道:“别看先生人很沉稳,就是用药火辣辣的,好的倒是快。”听大从打趣他,李慕道也放松了心情,说道:“我师傅只所以被称为鬼医,就是因为他的药,药到病除,可就是要多受几分罪。”
听了这话,梅香儒忍不住问道:“是不是配好药之后,再加几味让人受不了的。”李慕道听大人这样问不经愕然,心想我师傅又不是顽童,故意去捉弄人。
看看大人认真的模样只得答道:“并非如此,我师傅被称为鬼医,是因为他用药不同于一般郎中,常用些常人不敢用,或匪夷所思的东西。世人多不敢苟同。是以师傅虽然医术了得,却是毁誉参半。”
梅相爷听了,呵呵笑道:“我倒是很赞成他老人家这样,不墨守成规,任何事求新、求异才能有所突破。这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接着又问道:“我交给先生的事,先生办的怎么样了,招了几个人?”
李慕道听大人谈起正事,赶紧正颜道:“老朽尊大人嘱咐,在管事里招了两个能干的管理银钱,小的素来没有多余的银子,对这银钱一事也理会不得。大人的门客里有略通医术的,我招了十三个,府里的下人,有愿意跟着学习医术的招了八、九十人。这几天两个管事的正在寻合适的院子,寻着了,就正式开始教授。”
梅香儒闻言,沉吟一下突然对下面立着的小厮吩咐道:“去把管家叫来。”
梅香儒的脑袋靠在软垫上,趴得太久这会脖子已是不能动了,只得抬眼看看李慕道说:“李先生,鬼医和神医一样的病,可是一样的看法?”李慕道摇摇头道:“这一样的病,别说我们鬼医和神医各有各的治法,就是一般郎中也是百人有百样治法。”
梅香儒又问:“所有的郎中都能把病看好吗?”李慕道迟疑了下说:“每个郎中用药各有不同,治病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不过鬼医和神医用药不同,看好的却多些,名声也大。庸医却是十之有七、八。甚至有人只为骗取财物。”
梅香儒目光炯炯的望着他道:“爷让你汇编医书,就是要把同一种病的不同种治法,都记下来,给医者参考;让你广收弟子,就是让这世上多些良医少些庸医,那些庸医并非自甘坠落去做庸医,无非是无人教导罢了。让你寻些同道中人,也是要你们参阅学习别人的长处,对一些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可以共同去协商探究。一人智短,十人计长。”
李慕道恍然大悟般说道:“大人原来是如此用心,老朽明白了,一定不负大人所望。”
梅香儒却又说道:“这医术一道,博大精深,而一人一力终是有限,招募在医术有所成就的人,共同研究医道,再广传弟子,传播医术。这样才能把医学一道发扬光大。不拘于门阀,不拘于先后,不拘名声,鼓励弟子们大胆偿试,必有青出于蓝者。这医学一道才会不断进步。也只有这样许多现在看不了的病症也会得到医治。”李慕道听了这话如醍醐灌顶,顿感自己以前眼光太短浅,又拘泥于微名小利,思想也过于狭隘,豁然跪倒在梅香儒榻前,以头触地,道:“是老朽愚钝,没有领悟相爷大义。老朽定当竭尽全力不负相爷所望。”
梅香儒见他跪在地上,诚惶诚恐的样子,温言说道:“先生快起来,好好说话。这不怪先生,是爷没你说清楚。”
见李慕道站起来,又朝一边的绣墩努努嘴道:“先生坐下,我与你细细说明白。”李慕道这才正襟危坐。
梅香儒说了这许多话,身体已是有些疲赖。喝了几口茶,才又说道:“先生找个大些的院子,建个大学院,专门教授人医术、药学。先生、弟子除了现在招的,还可以发个告示,对外广泛招收,只要愿来,不计以前做什么?咱也不收费,先生月银还可以开高些;再建些医馆,由先生们坐堂,给人义诊,弟子们跟去学习。这学医实践最是要紧,每一个出师的弟子,都要能独立给人看病才行。先生、弟子可以按专长分开,比如说,给人接生的,治妇女病症的,治外伤的,治内伤的,治肠胃病的,我是外行,不懂你们的事,我只是个提议,你看着分。对于药学一项,还可以找些地,让学生们去种植草药。这学院,小了可以几百人,大了可以成千上万人。不要怕银钱不够,钱上爷全力支持先生。”
李先生听了,眼里已是金光闪烁,对相爷描绘的宏大的蓝图早已心驰神往。
正当他神飞天外之际,小厮一声通告:“管家求见。”总算把他拉了回来。
梅相爷叫管家进来,管家行了礼,梅相爷问:“咱府上可有大点的别院?农庄?”。管家道:“大人,府上的别院在京城的有九处,农庄二十多处,离这相府近得只有三处,不知大人做何用处?”
梅香儒微微换了口气,来缓解自己有些酸软的肩膀,又轻扭了一下脖子。一直默立在门边的兰心如见了,轻走过来,用手在他肩劲上轻按起来。
那手法娴熟,指间力道均衡,又恰到好处,梅香儒舒服的长叹一口气,不由夸赞道:“啊呀!心如好手法,可以出去开馆了。”
原本见他一个大男人长一双灵巧的纤纤素手,心下还觉得怪异。现在却由衷的佩服起来。
兰心如手指翻飞,嘴上却没说话,反而是李先生替他答道:“大人夸奖了,这雕虫小技那里能开馆!”
梅大人不以为然的说:“你只管招了弟子学这雕虫小技,以后你那学院没准还得靠这小技供养呢。”
李慕道心下道:大人大才即说这小技可以供养学院,必是有说道,哪是自己能明白的,我只按大人说的做必是没错,随恭声说了声:“是”
梅香儒望了眼精干的管家,也不同他商量,只吩咐道:“你派个人带着李先生和心如去别院和农庄看看。若是有他挑上的就把地契和人一并转给他。”说完也不等他答话,又冲李先生道:“你只管去挑,银子不够再给你支。你那医学院的名子我也想好了,学医者,最须铭记医德。叫铭德医学院吧!”说完又补了句:“现在就去吧!”
待李先生师徒去了,梅相爷沉默半晌,突然说道:“神医他们带走府里多少人?”管家应声答道:“丫环、小厮、婆子一供一百三十六人。”
梅相爷喃喃道“地牢的三百多少人放出去了。爷这一忽悠,这李先生再怎么着也能多带走个百八十号人。”沉吟一声又问道:“嗯……管家,若是这样,相府还有多少人要养?花费多少?”
管家以为爷又如以前般计较起下人的花费来,谨声答道:“大人,地牢的人是都送出去了。可是看地牢的狱卒还有壹佰多人在那,这犯人只管吃饭,又是猪狗食,花费不了什么,这狱卒却是要支月银的。这府里的下人满打满算走得不足三百人,可这相府光内府就有仆从二百多人,还不包括外府和农庄上的。护院有六佰多人,暗卫有多少人只有陈先生知道,估计也不在少数。”话还没说完,旁边的书童梅落笑嘻嘻的插嘴道:“爷忘了,咱府上光门客就有近千人呢!”
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听梅相爷产“哎哟”一声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时满嘴是血。
端水的,拿帕子的,下人顿时慌作一团,好一阵才消停下来。
梅落没想到自己随随便便说了句实话,大人就把舌头给咬破了,心中怪怨自己多嘴多舌。
梅香儒含了口水,漱了口,也顾不得疼,颤声问道:“平时管家的除了你,还有几人?”那管家道:“小的只是管理爷的府库支出,内院、外院、农庄、护卫、暗卫、地牢等另有人管,这管家大大小小也有十多位。”梅相爷接着问道:“这么多门客,怎么没有见一个过来出出主意,管管事的?”管家看了眼小凤,他立即明白这样的事,做为府库管家他是不便回答的。就接口道:“平时帮爷拿主意的有七八位,除了陈先生,都在耳房候着呢,这些天爷一直身子不利落,也没有传他们。爷要见,小的现在就去传他们过来。”
梅香儒微不可察的晃了下头,道:“我今天累了,明天一早,我醒了就都传过来吧,管家也都叫过来。”又神情沮丧的对管家说了句:“你也下去休息吧!”
任梅香儒放开想象也没有办法想通一个相爷养这么多下人、门客做什么?
原本他放大了胆子,也不过猜测这相府得有三、四百人。这已是他能想像的极限了。他更无法想像一个人要几百个仆人?怎么伺候?这太匪夷所思了。
今天他受的打击太大了,要不也不至于咬了自己。他本来想这么二下、三下就把人按排的差不离了。就算他下次再发作,受不了时咬舌自尽(如果咬舌可以死掉的话)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唉……现在这么努力连个零头都没取掉。这会他想死的心更盛了。没了精神气人也立刻萎顿下去。
在这房里最感丧气的还不是梅相爷,而是被相爷暗许为人中龙凤的小凤。
本来相爷一番话,不但吹热了李家师徒的心,也让小凤对相爷有了全新的认识,更是对相爷刮目相看。展望相爷所说的美好未来,他心中也是热血澎湃。就差热泪滚滚而下,漆黑深邃的双眸泛着烁烁的光。做为一个有理想的大好青年,他很愿意为相爷的宏伟事业添些砖加些瓦。
他的心刚升上天堂,又被相爷的那一句话‘爷这一忽悠,这李先生再怎么着也能多带走个百八十号人’打到了十八层地狱。闹了半天还是在算计花费多少?竟是比以前还恶俗了许多。这相爷是没救了。俗话说:“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这恰能用来形容小凤现在的心情。
梅香儒与小凤可谓失意人对失意人了,一个两眼无神看着头顶。因为如果他现在突然离去的话,势必是大胆的还能裹夹些财物走,而胆小的说不定连工钱也没处要。又有多少人家是指着这相府吃饭的。他真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就撒手而去吗?做为一个曾经的现代人,应有的社会公德心让他就这么甩手走的话即使去做鬼也无法安心,可要是都安置妥当的话,这么多人又怎么安置?唯一能让他有些底气的就是相府有足够的银子。想到这手心和额头都是汗了,浑身再使不出一点力气,仿佛一点一点地融化成了一滩烂泥。另一个人则是一双黝黑的眸子茫然四顾,仿佛找不到瞧点。失望从到脚底板泉水般涌上来,刚升起点对未来的期望又毁在这恶俗人的手上!
时间好像没有尽头似的,任由思绪杂念纷纷扬扬。
“大人……”梅落的一声喊叫,把两人从冥想状态拽了回来,抬眼看时,只见梅落人已到了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