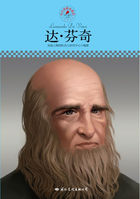韩愈在董晋、张建封等封疆大吏那里干得很不如意,因此,对前途充满了忧郁。这种忧郁长久积郁于心,又想到自己满腹才华,不得发挥,对上层官僚统治者们不由得渐渐产生出了一种愤懑之情。
正当韩愈准备递交辞呈时,张建封忽然差遣他赴京办事。韩愈觉得这是上京求职的一个好机会,他求官干事业的雄心再次燃起,于是欣然接受了张建封的差遣,迅速起程,北上长安,辞职的事也就搁下来了。
贞元十五年的冬天,韩愈到了京城,他四处忙着干谒之事,希望能够谋求一条出路。从中进士到现在以来的七八年间,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仕途,然而却碌碌无为,这使韩愈感到光阴的紧迫,不得不收起他高傲的自尊,求救于权门。但是权门深似海,他在长安城里始终找不着求升迁的门道。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恰巧遇到了与他同年登进士第的欧阳詹。欧阳詹是泉州晋江人,当时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他钦佩韩愈才华盖世,于是便想引荐韩愈,也没有经过仔细的思量,他便冒然率领国子监的数千名监生伏于阙下,向皇帝诉说韩愈的盖世之才,请求皇帝任命韩愈为国子监的博士。这一事件震动朝野。韩愈也想,这次有同年进士的鼎力相助,又闹出了这样大的声势,连天子唐德宗都知晓了,自己一定能在长安谋得一个稳妥的职位。
但这一请求未被唐德宗所批准。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德宗皇帝对他的一套很是反感,德宗皇帝需要的是浮华与艳丽,需要粉饰太平的文章,而韩愈所倡导的正好相反,加上对韩愈的这种聚众抬高身价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不给予官职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对于谋职心切的韩愈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对朝廷对君主的幻想,再一次受到直接而严重的打击。这是第一次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打击,因此在韩愈的心灵里产生了阴影。
其实仔细想想,韩愈的同年进士欧阳詹率国子监学生请愿,要求任用韩愈之事,确实是很不明智的。这种请愿,无疑是对唐德宗的不敬,认为唐德宗遗弃了贤才。作为天子的唐德宗,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他表面上对韩愈的才华很是赞赏,实际上已经对韩愈记恨于心了。韩愈毕竟此时尚缺乏政治见识,所以也只能任由同年进士导演出这么一件荒唐之闹剧。而且事过之后,韩愈还对欧阳詹的鼎力推荐十分感激,挥笔写下了《驽骥》一诗,以表达他对欧阳詹的感激之情。
《驽骥》诗中以两种马来比喻人的命运,驽马是劣马,骐骥是千里马。按理,人们应当喜欢千里马而讨厌劣马,但实际情况却相反,为什么呢?劣马能力小,身价低,也易于控制。更重要的是劣马很好喂养,因而颇受人们欢迎。骐骥就不同了,身价高昂辕食特殊,虽说本领超群,但不好驾驭,因此不受人们看好。诗歌中针对骐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借问价几何,黄金比嵩丘。
借问行几何,咫尺视九州。
饥食玉山禾,渴饮醴泉流。
问谁能为御,旷世不可求。
骐骥之贵,即便是堆成山的黄金也难买到;骐骥行之速,视九州如咫尺之间,骐骥非玉山之禾不食,非醴泉之水不饮;要找一个驾驭骐骥的人,旷世之中恐怕没有。所以骐骥在人间并不受欢迎,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也。
韩愈显然是以骐骥自比。由于现实善恶颠倒,是非不分,使有才饱学之士如骐骥一般弃置不用,无能之人充斥庙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面对这种现象,韩愈除了感叹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长安归来的途中,他平添了许多惆怅。
韩愈的骐骥之叹,表明了他对于封建官僚体制埋没人才的愤怒与反抗,显示了他强烈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不仅仅是针对世俗,而且更是直接针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可见韩愈叛逆性的超出想象的大胆。这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