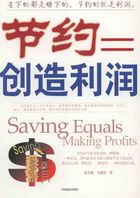克虏伯公司的领导古斯塔夫·冯·伯伦和哈尔巴赫从1941年起就得了重病,他只能很有限地参与公司的领导。
他越来越从公司的日常事物中退出来,并于1943年将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后来直至其终老,古斯塔夫没有再起积极作用。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得的是中风。
从1945年到1950年,他都只能躺在布律巴荷别墅邮房的一个小房间里,越来越不能动弹,他在那里等待着死亡,可死亡又那么长时间没有到来。而他旁边的宫殿成了美国占领军的宿营地。
尽管如此,当“千年帝国”的末Et和随之而来的克虏伯末日到来的时候,他还活着。而阿尔弗里德此时在威拉山庄。1945年4月11日,一辆美国吉普车来到这里,他被捕了。
1945年4月10日,就是希特勒在帝国首相府自杀前几天,美国第九部队的前沿部队来到埃森,他们中一些人是盟军智囊团的军官。他们凭借精确的地图,在埃森被炸的残破不堪的街道上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威拉山庄。这座建筑物毫发无损。在埃森的废墟中,它像是和平的绿洲,甚至公园的草还是那么绿油油的。当然美国人不是来看这些的。一名军官和两个士兵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跑上威拉山庄门前的台阶,对着房子喊:“克虏伯在哪里?”自从美国人进入了埃森的消息传来,阿尔弗里德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他在图书馆接待了美国人。“你是克虏伯吗?”军官有意如此无礼地问道。“是的,我是克虏伯·冯·伯伦”阿尔弗里德用纯正的英语礼貌地强调说。当军官冲他喊:“你被捕了”,阿尔弗里德连肩都没耸一下。根据管家的讲述,一个士兵给克虏伯公司领导戴上手铐,并把他带到了吉普车上。
像战后无数德国家庭一样,战争结束的一幕在冯伯伦家也开始了:阿尔弗里德被美国人拘捕;克劳斯在战争开始时是飞行员,在一次侦察飞行中被击落;哈拉德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一直呆到1955年;艾科伯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战死在意大利,只有一个儿子贝托尔特·在布律巴荷的父母身边。女儿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伊姆加特成了寡妇,瓦尔特劳特在寻找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被纳粹关在柏林。阿尔弗里德与他的国人唯一的区别是他的姓氏。这一事实的后果他会品尝到很多。
被捕后有人问阿尔弗里德,他现在对他的将来是如何打算的。在1945年美国人的耳朵里,他的回答听起来是莫名其妙的:“我当然要重建我的工厂,重新开始生产,您们知道,我是商人,不是政治家。”他冷静地但很轻松地回答。如果他以为,战胜国也会同意他的这个自我估测,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原以为,过不了几天他们会把他放出来的,事实证明这也完全错了。但他估计,他大约需要50年,才能把他的公司重建起来,他也错了。他的估计大致错在两点上:
他在监狱里一直呆到1951年,即差不多6年的时间,克虏伯公司的重建所需要的时间是他所估计时间的五分之一。
他只用了10年,而不是50年,就将克虏伯公司恢复了起来。
所有这些都还是很遥远的未来。阿尔弗里德在这之前是第三帝国的大人物之一,现在他必须学会在逆境中生存。
他太骄傲、太绅士了,以至于从不愿向人诉说他长年在监狱里的生活状况。与其他德国战俘所必须忍受的状况相比,阿尔弗里德所经历的确实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他来讲痛苦的是,他不得不无所事事,他没有办法履行他以为应尽的责任:建立公司,再给他的克虏伯人工作和面包。对他来说,与纽伦堡审判有关的事情也是很苦涩的。这两件事都使他越来越迷失了自我,使他更加不会与人进行自然的交往,更加内向、自制。他感觉,纽伦堡法庭上的审判不是公正的审判,而只是对战败国国人的一种报复,这种感觉他永远都无法去掉。后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康采恩,与战胜国进行了斗争。在对付战胜国时,他采用的一些手段非常有损他的名誉。而他本来是十分注重自己名誉的人。这些手段实际上是与他的个性很不相称的。但他丝毫没有觉得,他的手段是不公正的。关于这些,在谈及康采恩的解散时,我再详述。’
军事法庭原本要起诉的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冯·伯伦,因为他有一个令人憎恨的姓氏,并且他是克虏伯公司的老板。但当时古斯塔夫已经多年卧病在床,无法自理,他患有一种老年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越来越衰老。所以,他在1934年就将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1944年底,他已经无法与人交谈。1947年,如果要他出庭的话,同盟国的整个医生协会可为他做证明,他已经无法自理了。
有人建议,将阿尔弗里德代替他的父亲候审,但由于英国人对法律权力的敏感而失败。但仍有人在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上控告了克虏伯,他们试图证明阿尔弗里德和其它11位克虏伯公司经理是有罪的(在罪行问题判断上我根据的是库特·普里茨科莱特),这当然很不简单。单凭克虏伯公司制造武器这一点不足以成为罪证。因为国内外的许多公司都这样做了。另一个理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克虏伯公司的积极参与,使希特勒帝国的扩军成为可能,这个罪证也没有说服力。从1945年到1947年,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寻找惩罚克虏伯的理由。在这两年里,被告一直无缘无故地受到考察监禁。最后控方找到了四大罪状:被告犯有反对和平罪(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侵略战争);(为犯反对和平罪而)犯违背诺言罪;对占领区的毁灭;被告在军备生产中雇佣了“奴隶”(即战俘和强迫劳工)。
在前两个罪状上,1948年4月5日,被告被判无罪,而后两个罪状则不然。这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前两个罪状才是更根本、更严重的罪状。但因为对占领区的“毁灭”和“使用奴隶劳动”,阿尔弗里德和他的公司经理们被判处了最长达12年徒刑。法庭还没收了阿尔弗里德的所有财产。
对判决的解释长达167页。到底这个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这里不应也不能进行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的作者对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情况知之甚少(而且是在整个体制中最最一般的情况)。其中一个控诉说,被告如果拒绝使用“奴隶劳动”,最严重的不过是被送到集中营里。
但先不论如何评价这个惩罚,这个罪状根本没有考虑实际状况。首先,他们不“只是”受到威胁,作为惩罚,他们要被关进集中营里,而是要上绞架的。其次,党卫队和公司的那些纳粹信徒会毫不犹豫地将克虏伯工厂据为已有。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那些被迫劳工又会意味着什么?这应该是很容易描绘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境遇不会有所改善。
关于没收克虏伯公司的财产,甚至连法庭庭长都有些疑惑。他承认,这不仅完全不符合纽伦堡法庭迄今为止的审判,而且与一些公认的刑法都很矛盾。因为只有以不正当方式获得的财产,比如是偷来的,才能予以没收。显然克虏伯公司的情况不符合这个条件。
阿尔弗里德默默地冷静地接受了12年监禁和没收其全部财产的判决。此外,与其他被控告的克虏伯公司经理们一样,他也默默地忍受了漫长的审判过程,因为被告与他们的律师早就认为,这里的斗争所采用的是不合法律的手段。这些审判的法律基础是模糊不清的。此外,原告有两年的时间准备这次审判,而被告只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为自己准备辩护。阿尔弗里德请了位美国律师,因为他认为,他比德国律师更熟悉美国的法律。但法庭连他的美国律师也拒绝了。而他的德国律师却使他的当事人败诉。被告对审判的合法性本来早就产生了怀疑,而所有这些以及一些类似的事情,使他的怀疑更加坚定。
阿尔弗里德与他的经理们一起被囚禁在莱西河畔的兰德思堡监狱。他的狱友中有一位是艾瓦尔德·吕泽经理,他刚刚被希特勒囚禁过,他是戈德勒抵抗组织成员之一。他曾经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行动,暗杀失败。
这也是战后时期发生的矛盾之一。现在两个人与其他狱友一起被囚禁,与一些形形色色的犯人住在一起:有谋杀犯、外交官和将军。
阿尔弗里德当时的精神状态,我认为,用下面的一则逸事来描写,是最恰当不过了。一个年轻友好的德裔美国士兵,有一次问阿尔弗里德,他希望人们称呼他什么?克虏伯先生,还是冯·伯伦先生,还是他的全名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先生?“叫我克虏伯,”犯人回答,“我就因为姓克虏伯才来这里的。”他打趣地加了一句:“这个细胞是我在伟大的克虏伯遗产中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