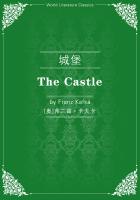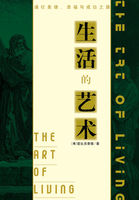实际上在娘家呆了不到四天,她心里就焦灼了起来。她有些惊讶,她没料到自己会是这样。我非住上一年半载不可,我要把你个老东西急坏,我要让你尝尝没婆姨的苦头。当时往娘家走时,她是这样想的。
她的娘家是一个很大的户,现时老一辈的人都没有了,但只是她的弟弟和堂弟就有十七八家子,加上侄孙辈,那可就是二三十家子了。她的娘家在马家村,整个马家村几乎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很为自己有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娘家而自豪而踏实。她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娘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娘家的女人你就一生是一个孤儿,你就是八十岁了,如果你没有娘家,你就还是个孤儿,你就只得受人家的欺负,给人家端尿盆,给人家的老人剪脚指甲,人家划出一大块麦田,让你一个人拔,你就还得拔。不要说没有娘家,就是娘家人弱一些,也还是对远嫁在外的女儿们不利的。女儿们在婆家的声音大还是声音小,那完全是由她娘家的势力强弱决定的。村里的男人们都有打老婆的习惯,有的男人简直把老婆往死里打,好像老婆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打着些才成,好像要打着些儿才能成为老婆。村里的男人们聚在一处,有时候竟还要相互吹吹打老婆的业绩。一次五旦说女人把门没有关好,让鸡把屎屙在面袋子里了,五旦并没有因这件事大怒起来,但五旦他还是抓着女人的两只脚脖子,把女人从自家门里拉出来,把女人倒拖着在村巷里走。巷子里是干硬干硬的黄土啊,巷子它凹凸不平啊,女人的衣服被蹭得缩了上去,女人的细嫩的脊背就在这硬硬的地上被拖着走,自然很快就烂了,有血流着,被拖过的地方,印着很多血迹。女人的头发都被拖散了,像一把被扯破的扇子,女人的指头铁索一样绞缠着放在小腹上,一颗头痛楚而无援地在自己的头发上滚来滚去。其实五旦他并没有大怒,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这证明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对待女人的。但他就这样倒拖了女人走,如果有人,他就要停下来,用有些豪气的声音骂女人几句,说这婊子不是人啊,让鸡把屎往面里头屙,细细的白面,她就让鸡往里头屙屎。说着,拖了又走。街上的人也有看了不满的,可谁愿意操这个闲心呢?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嘛。最当管的是那婆姨的娘家,可是那婆姨她有娘家吗?她只有个也嫁给人的姐姐罢了。后来还是她上去拦住了五旦。她说五旦你消消气也就成了,你还要往哪搭拖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她气得白了脸,似乎五旦拖的正是自己的一个亲人。她白着脸说,五旦你再不要这样,她给你生娃也生了一大群咧,没个功劳,苦劳总有些吧。她这样说的时候很多的男人女人都围了过来,奇怪的是大家一律地沉默着,大家都一律静静地看着她和那个五旦,看他们之间的事情如何收场。这时候那个衣服都被血和土染了的女人突然就用自己凌乱枯燥的头发裹住自己的脸恓恓惶惶地哭起来。她的一双脚脖子仍被五旦不大费力地抓在手里,她竟连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似乎是她乖乖儿地把自己的脚脖子给五旦抓在手里的,似乎是她乖乖地让五旦拖了她走的。女人恓惶的哭声让人感到很压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里也有了泪花,她有些哽咽地说,五旦,她给你儿子也养下咧,女子也养下咧,你要有个良心呢。她又说,是鸡屙下的嘛,又不是她屙下的。这原本是一句引人发笑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人笑。五旦自始至终是看着她的,大家也紧张地看着五旦,不知道他那样盯着她看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有些紧张,大家害怕五旦驴脾气一发,打她一个嘴巴,那可就真算是热闹了。不要说人家的男人,就是人家的娘家人虎汹汹地来上一堆,一人伸一个小拇指也把你戳死了。这样地对峙了一会儿,事情就有了结果,五旦狠狠瞪了她一眼,然后扔开自己女人的双脚走了。五旦的裤子那天垂下来很多,这就使得他的背面显得很落魄,甚至是有些可怜。五旦一边走一边往上提着裤子,大家普遍看见五旦的后脑勺原来很小,大家都觉得五旦那天的确是有些可怜。同时大家就都觉得她有些与众不同,是女人中的一个硬手。女人们都有些钦佩地看着她。其实女人们心里是清楚的,她所以敢这样,不过是因为她有那样一个娘家罢了,不然,像她这样只能生出一个丫头的女人,有什么资格在众人面前这样呢?其实她是清楚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清楚的,她就是凭这一点在女人当中做着一个硬手的。
但是天地良心,她的丈夫田志文却是不同于村里那些打婆姨的男人的,田志文从来不打她。她一直想把这事搞清楚,她觉得搞清这样一件事情的意义重大,但这事似乎就是一个谜,一个难以搞清楚的事了。但她还是倾向于丈夫怯于她的娘家人的缘故。他心里把我恨死了,恨得牙痛呢,他想拔我的头发,撕我的嘴,他肯定这么想,要不别的男人打女人他看着就不眼热?他肯定眼热得很。可是他不敢打,他一打,他就要想,人家的娘家人虎汹汹地来了我咋交代呢?他一定这么想着。她这样时不时在心里做着一些揣摸,心里不免是有些得意的,心里竟不时生出将他欺负欺负的念头。
记得结婚不久,她就听说了村里的男人们有打女人的恶习,她不免有些害怕,她不知他打她时她该怎么办。她记得一天夜里他们都比较高兴,她钻在他宽大的怀里摸捏着他微不足道的奶头尖儿,忍了半天,突然说,嗳,我给你说,你明儿可不能打我。原本是一句有些撒娇的话,可是说出来竟成了一句伤心的话,说出来她竟哽咽了,她竟很容易地就流出眼泪来。丈夫的两只大手在她的两只圆圆的、瓷瓷的屁股蛋上按了一按,使她和他更紧地贴到了一起。她清楚丈夫这是一个心疼她的动作,她的泪水就更活跃、更伤感地流下来了。丈夫附着她的耳朵吹气一般说,我不打你,我就是要咬你,说着丈夫轻轻咬咬她那时候还很胖很红的脸蛋儿。她摸一摸丈夫咬过的地方,浅浅地有着几个牙印,她的心里就有着一种奇异的感动和柔情,她想她得早早儿就把话说清楚,世事难测呀。她也轻轻地咬了咬他的奶头尖儿,说,反正田志文,我早早要给你说清楚,你要打我你就打,我的娘家人你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来找你,我可不给你帮忙,哪怕把你的耳朵揪掉我也不帮,咱们这是有话在先。丈夫当时听了她的话,老半天都没有说话。丈夫似乎在考虑什么。她也没有说话,她想这话必须是要说清的,这话一说,就不好再开口。丈夫却突然气恼地说,不说这话还好,你说这话,我偏还要打你。说着男人有些气恼地推一推她,翻过身去睡了。她那一刻深切地觉到男人的怀中和他的脊背是多么的不一样啊。男人的脊背是冷寂的沙滩,男人的怀抱却是温暖激情的大海。她对着丈夫呆板的脊背冷冷清清地躺了一会儿,心里很乱,很矛盾。她一时想讨好讨好他,让他转过身来,让他把自己再像一只小猫那样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整夜唇贴着唇睡觉。这些讨好的办法她都是有的,比如用舌尖顶顶他的耳垂,用他短短的头发极为耐心地编辫儿,把她的嘴贴在他的背上,不断地吹吹气,或者把自己脚的大拇指在他的脚板里蹭来蹭去,挠他的痒痒,不怕他不软了心肠,翻过身来搂住她的。这些想法都使她神往和陶醉,她极想这么干,但是她没有这么干。她深知这只是一时的快活,如果第一次这么干了,男人就会等着你第二次去挠他脚板的痒痒。她下了一个狠心,也转过身去睡了。然而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是被丈夫搂在怀里的。丈夫的脸是俯向她的脸睡的,丈夫的脸上有着某种哀怒和委屈。丈夫的模样使得她心里揪了一下,她觉得她是那样地疼爱这个搂着她的男人,她觉得昨天夜里自己的话说得有些重了。可是我给你不说也不行啊,万一你也是个手长的男人咋办?她心里说。发现自己又被男人偷偷地搂到怀里真是柔情四溢。男人还没有醒来,这很好,她可以把头轻轻抵在他的怀里流一些莫名其妙的眼泪。
在以后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丈夫果然是没有动过她一手指头。
漫长的岁月里,她有时会揣摸着想一些问题。她想,假如丈夫真的打她她会怎么样呢?娘家人果真要来找她的丈夫算账吗?想到娘家人蜂拥而来,一大帮人把她的丈夫压倒在最底下,她就觉得不寒而栗。她想极有可能,她是不允许娘家人这么干的,那时刻毫无疑问,她会和她的丈夫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给自己的娘家人一个尴尬。这一来就肯定把自己的娘家人惹下了,作为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娘家人惹下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不过也说不上,要是丈夫他真是打了她,到时候她就有可能和娘家人站在一个立场上,让田志文也尝尝她娘家人的厉害。
要是娘家人浩浩荡荡地打来,田志文他有什么招架的能力?他只有一败涂地。田志文他孤孤单单就一个人,连个姐姐妹妹都没有。有时候当她想到田志文孤孤单单一个人时她就觉得很是伤感。她做过一个梦,田志文打她了,田志文拖着她的头发在巷子里走。这自然就是了不得的事了。她跳起来就去找娘家人,娘家人很快就像潮水那样涌来,娘家人真是太多了,还有一些娘家人她简直都不认识,他们都怒气冲天地来找田志文了,他们要把田志文用乱脚踏死。
但是她突然就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她冲向了她的娘家人,她惨白着脸,举着瘦瘦的手臂劝她的娘家人都回去。她对他们这样一窝蜂地扑来突然有了深深的恐惧与不安。她拼力地推搡着跃跃欲试的娘家人,声嘶力竭地说,我们很好,谁也没有打我,你们回去。田志文躲在她后面,胆怯而求助地看着她,这使她对他有一种揪心的疼肠。她变了脸对娘家人吼道:回去,你们都回去,我的事不要你们管。娘家人大怒,一个没有看清面孔的人走上来,打了她一个嘴巴,然后他们在滚滚尘土里滚滚而回了。只留下她和丈夫在旷野上,一种莫名的辛酸与痛楚袭击着他们,他们紧紧地抱在一处痛哭了。这样的梦醒后,她察觉到自己的眼角是有泪的,而且她的心里也有着真切难言的酸楚,她就又莫名其妙地流出很多的泪来。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丈夫也从不曾打过她,娘家人也从不曾蜂拥而来,只是她自己一门心思地想着这些,动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情,流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眼泪而已。
而且直面丈夫时,她也没有独处着时有那样多的对他的体谅和柔情。在实际的生活中,她对他是有些厉害的,他自然不打她,但她也不允许他用重话说她。别的女人丈夫骂两句娘只要不动拳头就好得很了。她不行,男人从不骂她,这就使得她对伤害的程度与其他女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了,莫说是骂娘,就是丈夫重重说她一句,她都会有强烈的反应的。这一次之所以跑回娘家,也只不过是丈夫说了她一句,而她又以为这一句话把她说得重了。现在想想,那是一句什么话呢?值得跑几十里路来呆在娘家赌气吗?而且令她惊讶的是,仅仅在娘家呆了四天,她就有些焦灼不安了,时时想着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会不会也在想我啊。她一天一门心思就在他身上,不过她一会儿想他一会儿又充满憎恨。不过她的主意却是打定了的,暂时无论怎样,她都不回去,必须要他到娘家来领她,必须要让他来三次,那她才有可能跟他回去。她可不是一个没价值的人,这样一想,她就觉得自己还得踏踏实实地在娘家住下去。虽然她已经深切地体味到,作为一个离开娘家三十余年的女人,现在再不适宜在娘家久住了,她也不愿住在娘家,可她知道她必须还得住下去,还得做出长久住下去的打算,就当是坐监狱吧,因为他还一次都没有来过呢。你一次都不来请我就回去,我就那么贱?这是她的一个想法。我倒要考验考验,看在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又是她的一个想法。这两个想法对她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这两个想法都促使她在娘家住下去。我娘家二三十户人,我一家住上两天,几个月也过了,你个老东西就一个人轻松着吧。当她一个人时,她设想他是在她面前的,就这样对他酸酸地说。她想他要是真不来接她,那可真是不得了了啊。这样的想法比他的话更能刺伤她,她竭力回避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几十年的老夫妻了,别的不讲,只是夜里睡下,你摸摸左面是空的,你摸摸右面也是空的,你就受得了这冷清?哼哼,她想。实际上她是真的受不了这冷清了。
回到娘家时她就住在老娃家。老娃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这地方把家里最小的儿子都叫老娃。老娃住的就是老家,她做姑娘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现在老娃毁了原来的房子,又盖了新房,连院子也收拾了。因此她虽然明知这里就是老家,却常常就不能相信,回到老家时,心里就固执地觉得老家不在这里,而一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
老娃面相上也老了。老娃比她的锁儿只小半岁。她记得老娃那时候还吃过自己的奶,锁儿拼命地来推他,他口里含着她的乳头,眼睛瞪着锁儿,乳头却是怎么也不肯松口的,就把她的乳头扯得生痛。因为老娃吃过她的奶,她就对老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娘老子殁了之后,她一度奇怪地觉得自己的娘家不存在了。但渐渐地觉得老娃就是她的娘家,一想娘家,首先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老娃,想到老娃拼命吸吮着她的乳头,拿眼睛紧张地盯着他的外甥女锁儿的情景儿。回到老家后,她明显地感到了自己对老家的失望,同时,又有着更深切更伤怀的对于老家的思念。这真是很奇怪的。现在好了,回一趟家,蹦蹦车坐上,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样快的速度也使她有了一种难言的隐隐的怀疑,觉得用这么一点时间就回到老家是荒诞的,老家难道一直距离自己就这么近吗?
她记得她出嫁的时候,坐的是一辆拉拉车,四匹马拉着的。那可真是耍了一次不小的威风,四匹马的鼻前都戴着红花,马不时喷出潮湿而又清新的响鼻,四匹如龙的马呀,站在那里时都要焦躁地踏着蹄子。但就是这样的四匹烈马,把这一挂拉拉车拉着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她嫁到的那个村子。那时候就觉得是离娘家越来越远了,离娘家太远了,那时候以为是走到外国去了,再不可能回娘家了,心里的那个酸楚就不用提,眼泪一把一把地流啊。那时候回一次娘家是多么大的事情,要给青驴吃好饮好,再备些草料带上,人也是要带干粮要带水的。她骑在驴上,风总是吹着,但驴毛还是被汗湿透了;田志文像是梦游一样走在旁边,驴脖下的铃儿敲呀敲的,像是敲了有一千年一亿年。翻过一座山头又有一座山头在前面拦着,那些盘山的小路细得像是快要断掉。那时候回一趟娘家心里总是深情地想哭,就要见到大大了,就要见着娘了,就要见到年迈的奶奶了。像是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看到了自己生活过的那一小片村子,那个自己的娘家;把驴拽住,看一看,眼泪就狂奔下来了。为娘的喜颠颠地迎出门来,也是高兴得泪花飞溅的啊。
那时候回一次娘家就无异于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天堂。
她刚回到娘家后就想落泪,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她很清楚自己现在就是哭也不能放肆了,大家都好好的,你哭什么哭呢?不能让人有这样的想法。
她那天来时老娃不在,老娃买了一台补鞋机,用自行车驮了到处寻着给人补鞋。老娃的家里又脏又乱,不知养着几只鸡,院里到处都是鸡屎。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院里的一个果树坑儿积了些浊水,还没有干,老娃媳妇正就着那水洗娃娃的尿布。三个娃娃在她旁边耍着,最小的那个女娃独自在院子里爬着,手上、身上都沾满了鸡屎。
老娃媳妇看到她,站起来,把两只粗糙的胖手在屁股后面擦一擦说,来了大姐。声音淡淡的,似乎她并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似乎她常常来,昨儿就来过的,似乎她只是她的一个邻居。
她的鼻子陡然地一酸。
她就想,你跑到这里做啥来了啊。但她已经来了,她还得在这里住下去,短时间里还不可能回去的,她必须还得等着他来叫她。她想,如果他果然来叫了她三次,那么最后一次,她就跟他回去,她会因此而对他充满感激之念。她想,如果这一次他果真叫了她三次,那就算是他给了她面子,从此以后,她一定要事事听他的了,洗脚水都可以端给他的。
她担心地想,他会来叫我吗?
但是她又有些果断地想,我就是要看看你来不来叫我,你要是不来叫我,那咱们两个的事情可真就算是大了。这样一想,她就觉得自己的做法并非胡来,应当说还是很值得这样做。等着他来叫她已经成了她很大的一个念想。他第一次来,我先得给他一个背子,让他站在我后面求我,第一次干脆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脸;第二次嘛……这个女人是这样子作着她的计划的。
因为有着这样一个长远的计划,因此她对老娃媳妇说,她的丈夫走哪搭哪搭了,一时半会回不来,她呢一个人呆着心慌,就浪娘家来了。这一次可以好好浪浪娘家了。她讪笑着说。其实她心里是很酸楚的,她想老娃媳妇毕竟和自己生分,毕竟难以做到和自己心贴心,因此与她说话,越是关键的话就越是得撒谎。这就使她有了一种独自干着一件大事时的孤寂感。要是娘在,用得着一见面就撒谎吗?要是娘在她肯定会把一切想法对娘说个清楚,和娘一同谋划着完成这件事情。那时候娘多么指望她在家里多呆几天啊。娘一天几趟地到草窑里看鸡下没下蛋,然后煮熟了给她吃。但这是娘,娘就是娘,谁都不能比的。
娘殁了,大也殁了,她还有个谁?往心里说,不就剩下个他了吗?
因此她就得考验考验他。
做饭时,老娃媳妇从米袋深处剜出两个鸡蛋,要为她打破,她很严厉地阻止了。她摊开心一般说,老娃媳妇,你不要把我看外,你们吃啥我就吃啥,你要给我另做,我就不好住下去了。她说,蛋不敢吃,放下卖钱。
其实这也只是貌似真诚的话,要是为娘的给她打蛋吃,她就不会讲这些似乎很真诚的话了。蛋终于没有打。果然是吃了一顿便饭。这使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她想一周之后,他可能就来叫她了吧。再叫上两次,也就是半个月,二十来天的时间。二十来天都在老娃家吃饭不大合适,办法是有的,她可以住在老娃家,至于吃,她可以在几个弟弟家里巡回着吃的,而且堂弟家里也得去,不然他们就会说闲话,去一次两次,不至于惹得他们烦吧。
吃过饭,她拎了锹,把满院的鸡屎一概铲净。她对老娃媳妇说,你有啥活计我可以帮你做的,老娃媳妇就向她友好地笑了笑,这使她很高兴。下午,她到另外几个弟弟家走了走,不然他们会说闲话的,会说她看不起他们。她回到老娃家时屋里已亮着灯了,马家村是风力发电,电弱,灯总是昏黄着,不大亮。老娃已经回来了,蹲在门槛上,用油污了的手握了筷子吃饭,眼睛睁大了盯着碗里的饭,似乎在惊异于饭的迅速减少。老娃站起来向她打了个招呼,又蹲下吃饭。她却突然地由老娃想到了娘,娘那时候是怎样地疼这个娃呀,他不喜欢吃馍馍皮,娘就一下一下将馍馍皮剥尽,给他吃,他要是发现馍上还有一小点皮儿,就会把馍馍掼到娘的怀里,躺下了打着滚哭。现在他还把馍馍剥了皮吃吗?谁给他剥呢?这样想着,她的眼泪险些儿落了下来。老娃买了点梨子,梨子和老娃的手一样脏。老娃说,姐你吃梨子去,她吃着梨子,心里总是觉得很酸。
夜里她和一个侄儿睡在一间小屋子里。侄儿后来逃到她娘那儿去了,就剩了她一个人睡。她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单。从来都不曾一个人睡过,从来都是旁边有一个人的,有一种熟悉的呼吸的,从来都是睡在一个人怀里的。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离开他第一夜,就开始这样强烈地想他,似乎他不在身边,自己就成了在荒原上迷失了方向的人,她感到自己茫茫无助。越是睡不着,她就越是觉得她离开他已经很久了,她像是隔着一域茫茫的水面再也望不到他。
她翻过身去睡了,这样就会使她觉得他是睡在她背后的,而且是她生了他的气,她不可能把身子转过去的。
她想不通丈夫那天为什么要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他或许是没话找话吧。原本家里平平安安的,她坐在炕上给他纳一只鞋底子,他蹲在门口就着照进门里来的那一缕阳光拧一根皮鞭子。阳光很亮,他一拧紧,鞭子被拧紧的地方就渗出黑亮黑亮的油来。她听着长长的麻绳穿过鞋底的声音,心里感到一种异常的安宁。
可是他突然就说出了那句话。
他把鞭子拧得一冒油,等那油再度暗下去,他就信口开河似的说,唉,我问你话,你可要给我说实话。她还是专注地拉着她的麻绳儿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但她的耳朵支棱起来了。他又把鞭子拧得冒了一下油,他说,你说实话,过了这几十年了,你觉着,现在,对你来说,我和你的娘家哪个更重要些?原本这就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原本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他原本或许也是无意问的,问出来了,他似乎觉得这问题问得好,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把头抬起来,说,说呀,我和你的娘家人谁重要?两口子之间总是要问一些荒唐的问题的,而且往往会答非所问,令对方失望。她又一次把长绳缓缓地拉过鞋底,将绳子在自己的手上缠得密密匝匝。他望着她,说,说呀说呀,咱们一边说话一边干活计嘛,这么孤死了,你说哪个重要?平心说,撒谎就是狗。她把手背上的麻绳子抖开,她说,你说哪个重要?我要你说嘛,我说我就不问你了。显然丈夫已对这事认真了,他已经停了拧鞭子,只是将她直直地望着。她用锥子将鞋底扎开一个眼,然后将针穿过去,悠悠地拉着麻绳儿,她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清楚自己一定会怎么说。她说,当然是我的娘家重要啊,你是不是以为你重要?她这样用玩笑的声音说。她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有着一种难言的快意。丈夫的头低下去了,他又开始拧鞭子。阳光很好,他不断地将鞭子拧出油亮来,但是他突然停住,抬起头说,你说你娘家人重要,那你就跟你的娘家人过去吧。这话就使她生出一些淡淡的气来,她想咋能这样说话呢?她想说,凭什么叫我的娘家人养活我?你是干啥的?原本这才是心里话,这样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可是一出口,话就成了这样:过就过,你以为我娘家人养活不了我。这样的一说,声音里明显是有着一种情绪了。丈夫说,你娘家人咋能养活不了你呢?你那么大的一个娘家,这一家吃三天,那一家吃五天,半辈子就过了。她冲口说,就是就是,不靠你我也能过得去,不用你操心。一时半会儿就将话说成了这样,而且拿针的手竟微微地有些抖了。
夜里他伸手来抱她,她原本是等着他这一手的,想他只要手伸出来,哧溜一下,她就扑到他怀里去,好好用牙咬一咬这老东西。可是他的手真探到她身上时,她却滚了两个过儿,离他很远睡下了,并且就给了他一个背子,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她背身在远处躺着,心咚咚咚跳得厉害,但是这个狠心的贼,他再没有来抱她,他为什么不也翻两个过儿呢?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他要是再滚过来,再把手搭在她的身上,没说的,投桃报李,她知道自己会怎么干的。但他竟没有滚过来,他竟也是翻过身去睡了。这使她觉得她受了他的欺侮和愚弄,她有了一个复仇的愿望。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她已经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她把纳了一半的鞋底用一块白布包好,放在炕边上,她似乎一直坐着在等什么。看他醒来,不解地看着她时,她心里掠过一丝快意。她说,你醒来了,我就给你说一下,老娃带信来了,说是宰了羊,让我回去浪几天。丈夫审察地看着她,突然一笑说,老娃几时给你带的信?老娃连夜给你送信来了吗?我咋不知道?丈夫的神情和语言都使她很不满,她说,我不跟你磨嘴皮子,我还要赶车去呢。说着抓了炕边的鞋底就走。但她很快又返回去,丈夫说,羊肉吃罢了吗?她什么也不说,红着脸,把手里的鞋底儿扔到了炕上,然后看也不看他,就夺门出去了。
一会儿,当她坐在令人担心的蹦蹦车上时,日头已经升了起来,路两边的庄稼上的露珠闪闪地发着亮光。有人赶着羊往山上走。她忽然觉得心里很渺茫很难受,她闭住眼睛,咬着嘴唇,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流下眼泪来。她向路后面看着,她希望他来追她,但越来越长的路面上一直是空荡荡的。
她几乎有了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的打算。
两个礼拜过去了,也没有谁来请她回去。她开始坐卧不宁了。她开始胡思乱想了。她深切地体味到娘家是不宜久住的,她就像已经落下来的树枝,再不能长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她虽然也在老娃家做活计,但她总像是一个外人了。做活计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仆人,吃饭时她不好意思大大方方地去搛菜,她也不能无所谓地把一碗饭吃完,总是忍不住要看老娃媳妇的脸色。老娃媳妇原本就是一个冷脸人,她是知道的,但现在她觉得老娃媳妇的脸只是冷给她看的。她来之后给老娃媳妇是帮了不少忙的,首先是院里再不见鸡屎了,她建议老娃媳妇盘个鸡圈,结果只用了半天时间,她当大工,老娃媳妇当小工,就修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鸡圈。她在老娃家忙碌着,扫地、扫院、做饭、洗锅,什么都干。她把老娃的家里扫得干干净净。其实她在自己家里也没有这样勤快。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她忙活时,老娃媳妇会说,姐你缓着去吧,但是谁听不出来这是假话呢?老娃也希望她这个当姐姐的忙活一些,好叫自己的女人不在自己跟前说闲话。她是很明白这些的。老娃有时觉得负疚,会趁着女人不注意时偷偷抓一把葵花子给她,偷偷递一个果子给她,她被老娃这样的动作搞得很是辛酸。而且她有时还要去河里给老娃家提水,这一来就叫其他的弟弟弟媳看到了,弟弟们就算不说什么,但弟媳们却一定是要说什么的。她是女人,她知道这些。就搞得她连其他弟弟的门也不好进了。你给老娃家做活计,你就在老娃家吃饭吧。她似乎听到其他的弟媳们这样说。她还不能得罪了她们,问问她们可有什么针线活计让她帮忙。她们自然就是有的。她身边已经有着二弟、三弟的两双鞋底子了,很厚,她都答应了,她答应为她们纳鞋底子,她一边纳着鞋底子,一边就想起丈夫的那双纳到一半的鞋底子来。她想自己真是臭毛病太大了,为什么要把那鞋底子扔下呢?不然现在也纳成了。而且由于她在老娃家里给老二、老三纳鞋底子,她又怕引起老娃媳妇的一些看法。一边受苦,一边还要处于各种矛盾之中,这使她觉得很是痛苦。你这是何苦呢?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就问出满眼的泪花,还不能把它们畅快地流出来。尤其在夜里,一个人凄凄清清地睡着时,更是要这样地问自己,硬是要问得自己一个泪流满面。她夜里总是睡不着,夜里她的念头异常地活跃,夜里她咬牙切齿地想着那个人,想到他她的牙根就痛起来,鼻根那里酸得厉害。她用最毒的话骂他,她对他说,我究竟把你咋的了,你这样地整治我、欺负我。她认为丈夫在那边按兵不动完全是没把她放在心上,完全是在欺负她,是在用最狠毒的方式欺负着她。她似乎看见丈夫在那里心平气和地喝着茶,心平气和地坐在杏树下阴凉着自己,她恨透了,她想一拳头打飞那个茶杯,她想一顿乱脚把他从树阴下踢开。一到夜里,一想到丈夫那边的寂静无声,她就觉得自己像一盆烈火那样怒火冲天地燃烧起来。原本她觉得是自己制作了一个游戏,现在,她反而觉得是丈夫不动声色地搞了一个游戏,自己反而陷身在他的游戏中了。她甚至在某一刻突然有了一种将丈夫杀掉的强烈愿望,先杀掉他,再杀掉自己,她觉得这样的杀掉是丝毫没有什么疼痛的,反而有着一种很强的快感。当这一阵疯狂的情绪掠过后,她觉得自己累极了,滚烫的眼泪顺着腮边直流,打湿了枕头。她在心里哽咽着对他说,我究竟是怎样惹了你,你竞这样地欺负我呢?你为啥不把我叫回去?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没有一天不等你,你咋就不来?你为啥不来?为啥吗你?难道我不值得你把我叫一叫?难道你真的就一个人过活着好吗?你来把我叫叫,能少个啥?蹦蹦车坐上,两个钟头就到了嘛。我一个女人嘛,我的面皮子总比你一个男人薄吧?你来把我一叫,咱俩一同搭上蹦蹦车回去,那该多好。你偏偏儿要把个简单事往复杂里搞,偏偏要把个事搞僵你才满意,你咋这么个人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是事情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展,她不得已改了原来的计划,三次的话就不再说了,只要他来叫两次也行了,第一次拿拿架子,第二次就乖乖儿跟他回去。她有时想到他们两口子隔着这么远一人孤孤单单地睡一间房子,简直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两个人睡在一起,很多时候她都是睡在他宽大的怀里的,似乎那里是她的一个安乐窝。刚成家那些年,他们一个把一个多么稀罕,什么是家?一个就是另一个的家。丈夫的怀抱就是她的家,她的身体就是他的家。有时候一个把一个喜得不行,没办法,就只好将嘴贴着嘴睡到天亮。天亮了,纸窗上像镀了满窗暖暖的金子,贫寒的屋子里奇异地富丽了起来。那时候他会干这样一件事情,他会突然地拉去被子,他们都是裸着身子的,年轻的胴体被纸窗上的阳光一映照,他们都觉得自己和对方的胴体都是极美极健康的,那自然是要在一起再抱一会儿的。落满阳光的年轻的身体互相地爱抚在一起,那真是很让人神往和回味的啊。现在不行了,老了,自知之明,天亮了,再不敢将被子用力拉去了,在被子底下一个将一个疼肠着吧。年轻的时节,他好用一双大手揽住她的一对圆圆的瓷瓷的屁股蛋儿,她则喜欢握着他的生命之根,她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她握的是自己丈夫的嘛。她因此而觉得踏实,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安宁感。后来一上岁数,他们肉体上的亲近少了,但似乎一个把一个却更疼惜了,睡觉时即就是穿着衣服,也是他把她搂着,她像一只小猫顺从在他怀里。
可是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呢?她真怕自己一不小心连自己也不能控制地逃回去。但她想再忍一忍,再忍一忍,说不定明儿他就会来领你的。
一天夜里,忽然她发现他和自己睡在一起了,他哀怨地看着她,像在埋怨着她的绝情。她一时觉得鼻子似乎都酸掉了,什么都不答,什么也不问,一头就扎入他的怀里去,她两手到后面去搂住他,他也搂住她。久违了,真是久违了,他又用两只大手揽住了自己的屁股蛋儿,似乎屁股蛋儿又成了年轻时候的样子。他附着她的耳朵说,小妖精(这是她年轻时他常常这样悄悄地坏坏地喊她的),小妖精,我可不能让你再跑了。她说,我再不跑了,你打我我也不跑了,你把我的腿打断吧,这样我就不能再跑了。她又一次握到了她曾经握过的东西,依然是壮硕的,她幸福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是她把眼睛睁开一看,窗纸惨白着,天快要亮了,炕上却是只有她一个人。
这个梦做完后又过了好几天,女人盼着领她的那个人还是没有来。这时候田地里的麦子在阳光的激情里一天比一天更黄了。
后来她的女婿到马家村来过一次。说不清为什么她见到女婿时竟是泪如雨下,她用了极大的克制才使泪水没有狂泻,她只是用一块旧旧的手绢不断地沾着自己的眼睛,使那手绢像水洗了一样。女婿是来叫她回去的,女婿说我姨父在那边一个人不方便,你在这边也不方便。她问女婿谁叫他来的,女婿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不知道丈母娘的用意,他老老实实地说是锁儿叫他来的。他说原本锁儿亲自要来的,可是娃娃缠着,不得来。女婿说,姨娘,你要回,我堵个车把你送回去。
她毫不犹豫地就把女婿打发回去了,她对他说,她不回去,她要一辈子住在娘家了。当时老娃媳妇在场,她就不知不觉地用了比较大的声音说,我的娘家人还是养活得了我的。老娃媳妇什么也没有说,老娃媳妇只是感冒了一样抽了抽鼻子。她就有些辛酸。她对女婿说,你回去吧,我们的事你们不要管。女婿就一脸沉重,他一定觉得丈人和丈母娘之间有了了不得的大事了,他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回去了。很快女儿又来了一次,女儿瘦得很厉害,女儿当着她的面大哭了一场,女儿说妈你看你瘦成个啥样子了。女儿拿出一面小镜镜给她看,她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她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瘦成了那样。但是她对女儿说得很明白,她不回去。她也流了泪,她说,锁儿,不是妈不回去,你大这个人,他的心太歹毒了。女儿要问个究竟,她说,我们之间的事是说不清楚的,你回去吧,你不要管。女儿忍了半天突然问,妈,总不是我大又找了新的女人吧?女儿的这句问话像猛兽咬了一下她的心,她一时竟是脸色煞白,她问,谁给你说的?女儿说,我不是在问你吗?她说,倒不是这样的事,你回去吧,妈知道该咋干的。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女儿说,妈,那么你到我那搭呆几天吧,我舅舅这搭不方便嘛。她心里一动。可她马上就否定了自己,女儿家是不能去的,要是去了女儿家,他就要问,咋没住在你娘家那里啊?娘家总还是靠不住吧?
这就要丢娘家的脸。
把女儿打发走了,对丈夫又生了仇恨,很大的仇恨,他越是不来叫她,她越是觉得他成心是在气她。她想莫说他来叫三次,就是叫十次她也未必会回去了。
我要让你死的时节没人侍候你,她恶毒地诅咒他。
那时候麦子迅速地黄了。
别人都在拔麦子,于是她便起早贪黑地帮老娃媳妇拔麦子,她不能帮老娃一家拔吧,都是兄弟,你咋就给老娃一家拔呢?弟弟们也许不说,弟媳妇们却一定是要说的。于是她就给老娃媳妇赔着笑脸说,再的你拔吧,我给那几家子帮帮忙去。她在这家拔两天,在那家拔两天。她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身份了。就这样她的心还是不得闲,一边拔着娘家的麦子,一边想着自家的麦子,自家种了十几亩麦子呢,他一个人咋拔得了啊。想想年年他俩肩并肩地拔着,信口地说着话,那是多么好啊。有一刻她心里就燃起大火来,她会突然质问自己,我怎么能在这里拔麦子呢?我这是何苦啊。快快地拔几把,到前面去,让泪水好流下来。这时候弟弟们也开始劝她,让她回去拔自己的麦子,可是她怎么能回去呢?她觉得刚来的时候倒可以回去,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回去了,现在确实成了一件不好处理的大事。现在必须要他来请她,她才能满心酸楚地回去,不然她就只有在娘家呆一辈子了,想到要在娘家呆一辈子,她真是不寒而栗。
这一年,她拔的麦子最多,她给五个亲弟弟家都拔了,她拔废了几双手套子,最后把自己的手拔得不成样子。麦子拔完后,用这样的手,她还奉命纳着弟媳妇们拿来的鞋底子。
这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让人大开眼界的事,他们马家的一个女子,被女婿打了一顿,引得整个马家倾巢出动,把那个打人的小伙子连同他的家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好几天来,整个马家村都兴奋无比地谈论着这件事情。据说老娃只一拳就把那方面一个人的牙打断了一颗。老娃有些余兴未尽地对她说,姐,我姐夫他要是敢惹你,我就打断他的牙。这原本是很鼓舞她的一件事,但她却显得无动于衷,她甚至对老娃这样说有些反感了。
渐渐地村子里有了些闲话,说是她丈夫看不上她了,要跟她离婚了,她不知这话是谁先说的,但这话是在马家村传着,马家村就是她的娘家。弟媳妇们看她时渐渐都有了一种别样的眼神。女人对女人的某些怜悯简直是可怕的。
我的掌柜的,我的男人,你快来把我领上走吧。
她几乎是在心里这样高喊着了。
天气一天胜似一天地有了凉意,秋声渐渐地逼来,雨也就跟着连绵起来。这样下雨的天气,屋里尤其显得暗,人总是觉得屋子像是一个个不祥的大蜘蛛。
那天落了一夜雨,到早上仍然下个不停,她一个人在这边的屋子里躺着,觉得炕很凉,屋顶很黑,屋外的细雨下个没完没了。她不想起来,她就想那样躺着,后来听到谁在喊她吃饭,她说不吃,也就再没有人喊了。她就那样呆呆地躺着,听着风在雨丝里凉凉地掠过,谁家的牲口用很长的声音绝望地叫着。
她这样地躺着,不知什么时候,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突然,她听得门啪啪啪响,以为是梦,惊醒后只听见老娃在外面火烧火燎地叫,像是有什么急事。她猛地坐起来,心急急地跳着,她赤着脚开了门,见老娃后面立着一个人,是她的邻居,从他脸上她看出似乎有着很大的事情。
果然是出了大事。
她那个邻居是来送信的,说她丈夫今儿早上从房上摔下来了,摔坏了。这里的摔坏了就是说人已经没命了。
她的头嗡了一声,她又凄厉地叫了一声,就赤着脚跑入雨里去了,跑远了。老娃拎了她的鞋,在后面追着喊她把鞋穿上。但她却是疯了一样在密织的雨丝里跑远了,使得越跑越远的她像是一个幻影,但她凄厉的哭声却是异常真切的,她的哭声似乎惊动了上天,雨更大地下起来,村里的人们都被这哭声惊得冒雨出来观看。雨很大,已经是看不到了,只是从雨的深处传来她那异常凄厉已有些沙哑的哭声……
咋能由房上掉下来呢?
这么大的雨,上房去干啥呀。
村里人这时已渐渐得了音讯,就躲到雨淋不到的地方,这样地议论着。
后来他们去送葬,就得到一个更为确切的消息:原来田志文近日来有了一个习惯,他时不时就到房上去,坐在房上往远处看。有时候他能向远处望上一整天。大家都认为他得什么病了,但是没想到下雨天他也往房上走。
在葬礼上,雨还是没有停,好在雨小了很多。人们都看见那个逃离村子很多天的女人用一只没有纳完的鞋底子不停地捂着自己的脸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