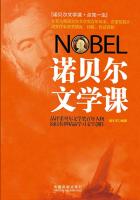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对人性以及心性关系问题作了探讨。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他还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论。后来的荀子则提出性恶论。宋明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心性论。王廷相在探讨心性论问题时,明确提出“性与气相资”、“性生于气”的观点;并主张性有“善恶之杂”等,在元气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心性论体系。
一、性与气相资
人性的来源问题是心性论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张载明确提出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他认为,天地之性是人禀太虚之气而成,气质之性则是人生成后因气质的差异而形成的,但都是以气作为人性的来源。程颢、程颐认为,应从理气关系上来讨论人性的本源问题,“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二程遗书》卷六。)。“天命之性”就是理,“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实际上二程是以理言性。朱熹发挥张载、二程的思想,强调“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四。)。王廷相则明确主张“性生于气”(《雅述》上篇。),与上述诸观点都有所不同。
(一)性生于气
朱熹说:“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横渠理气辩》转引。对朱熹之说,王廷相作了具体分析和发挥。王廷相说:
由是言之,则性与气原是二物,气虽有存亡,而性之在气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气之聚散而为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义礼智,儒者之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故有生则有性可言,无生则性灭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无,缘于气之聚散。若曰超然于形气之外,不以聚散而为有无,即佛氏所谓“四大之外,别有真性”矣,岂非谬幽之论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精神魂魄,气也,人之生也;仁义礼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觉运动,灵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贯之道也,故论性也不可以离气,论气也不得以遗性,此仲尼“相近”“习远”之大旨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横渠理气辩》。
王廷相的这段言论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了性与气的关系。
首先,性是与生俱来的。“有生则有性可言,无生则性灭矣。”王廷相认为,儒家的所谓性,即仁义礼智,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是人心知觉运动的结果;无人,即无心;无心则无性。他又说:“《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性由于生,道由于性,明且著矣。”《雅述》上篇。“人有生,则心性具焉,有心性,则道理出焉,故曰‘率性之谓道’。”《雅述》上篇。可见,性源于生,而不是独立于人生之外的东西。“性”字在甲骨文中是下地上草,即草木在大地上生长,故性有生意。性本字为生,后来演化为性。
其次,气是性的根源。针对朱熹答蔡季通所说的“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王廷相说:
即此数言,见先生论性辟头就差。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是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矣,一贯之道,不可离而论者也。如耳之能听,目之能视,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无耳目,无心,则视听与思尚能存乎?《雅述》上篇。
王廷相认为,性不是独立于气之外的一物,与气合而为人;“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矣”。他还明确主张:“性生于气,万物皆然。”《雅述》上篇。
再次,性气相资。“论性也不可以离气,论气也不得以遗性。”对于程颢所说的“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王廷相称之“于性极为明尽”(《雅述》上篇。)。在程颢论说的基础上,王廷相进一步说:
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王廷相认为,人的本性是人的气质所为,仁义礼智之性为人心所具有,并为知觉运动而表现出来,离开了心,就不存在性,所以论性不可以离气,论气不可以遗性,性气不相离,相互依存,统一为一个整体。
王廷相的“性生于气”、“性与气相资”的观点表明,他与张载一样,是以气言性。但是,张载在以气言性时,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且认为此二性来源于不同的气,以至于后来的朱熹以理言天地之性。王廷相排除人有二性的说法,并否定以理言天地之性,实际上也否定了张载的天地之性的说法,将以气言性贯彻到底。王廷相在形成以气言性的思想过程中,也吸收了二程的某些以气言性的观点。但是在二程那里,理比气更为根本,并且“性即理”是二程解释性的本源的基本观点。因此,王廷相的以气言性与二程的以气言性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他们各自的哲学路线是不同的。
(二)对性即理的批判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的心性论对人性本源问题的基本回答。王廷相在提出他的“性与气相资”的观点时,对“性即理”以及人有天地气质二性等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诸儒避告子之说,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天下,而分辨于后世,亦夫人启之也。”《慎言·问成性》。告子,战国时人。《孟子》中有“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王廷相并不否认他的观点与告子一脉相承,并且以此反对以理言性。王廷相说:
《易》曰:“穷理尽性。”谓尽理可乎?《孝经》曰:“毁不灭性。”谓不灭理可乎?明道《定性书》之云,谓定理可乎?故曰气之灵能而生之理也。仁义礼智,性所成之名而已矣。《慎言·问成性》。
王廷相认为,“理”与“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特定的内涵,不能相互混淆,亦不可相互置换。
关于性与理的关系,王廷相认为,《中庸》所言“率性之谓道”,指的就是道出于性。王廷相强调:“性者缘乎生者也,道者缘乎性者也,教者缘乎道者也。”《慎言·问成性》。“性与道合则为善,性与道乖则为恶。是故性出于气而主乎气,道出于性而约乎性。”《慎言·君子》。认为理是性之理,并非性本身,因此,性理并非完全一致。
所谓人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的观点,始于张载,成于朱熹。但是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是禀太虚之气而成,而朱熹的“天地之性”专指理而言,二者有所差异。在王廷相看来,以为人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此宋儒之大惑也。并且,他否认所谓超然形气之外有本然之性的存在。
王廷相认为,人有生,才有性可言,因而“是性之与气,可以相有,而不可相离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于气焉载之”(《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性辩》。)。接着,王廷相又以“圣人之性亦不离乎气”论证性气不可相离。他说:
今夫性之尽善者,莫有过于圣人也。然则圣人之性,非此心虚灵所具而为七情所自发耶?使果此心虚灵所具而为七情所自发,则圣人之性亦不离乎气而已。性至圣人而极。圣人之性既不出乎气质,况余人乎?所谓超然形气之外,复有所谓本然之性者,支离虚无之见与佛氏均也,可乎哉?《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性辩》。
关于宋儒所谓人有二性的观念,王廷相认为是其来源于对孟子性善论的牵强附会。“性生于气,万物皆然。宋儒只为强成孟子性善之说,故离气而论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后世,而起诸儒之纷辩,是谁之过哉?”《雅述》上篇。性与气相资,而亦有不得相离者。但是,以气质言性,则性必有恶,那么孟子性善之说就不通了。因此,宋儒为了自圆其说,又“强出本然之性之论,超乎形气之外而不杂,以傅会于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论反为下乘,可乎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这就是说,宋儒的所谓超然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完全是为了附会于孟子的性善之说。对于宋儒所谓的人有二性的观念,王廷相还进一步指出其认识论的根源正是在于性气相分。朱熹说:“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而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是气,性自是性,亦不夹杂。”《朱子语类》卷四。王廷相直斥朱熹此论杂佛、老之言:“信如诸儒之论,则气自为气,性自为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韩子所谓‘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者是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程朱理学心性论的宗旨是与佛、老心性之学相抗衡。朱熹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又说:“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朱子语类》卷四。而在王廷相看来,程朱理学离开气而言性,以为有超于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仍没有与佛氏的心性之学区别开来。王廷相说: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执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众生皆有本觉,谓本性之灵觉处,虽流转六道,受种种身,而此觉性不曾失灭,故以此为真性、为圆觉。其有生而能解识者,为众生悟入知见皆从觉性生出,故云圆觉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罗蜜。菩提,觉也,无法不知之义。涅槃,圆寂也,谓觉性既圆,无法不寂也。波罗,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谓离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永归寂灭,不生不死也。由此观之,佛氏之大旨尽矣。儒者不达性气一贯之道,无不浸浸然入于其中。朱子谓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其实自佛氏本性灵觉而来,谓非依旁异端,得乎?大抵性生于气,离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养修真气,虽离形而不散,故其性亦离形而不灭,以有气即有性耳。佛氏既不达此,儒者遂以性气分而为二,误天下后世之学深矣哉!《雅述》下篇。
王廷相说程朱理学的心性论未脱佛老心性论之旧巢,这是击中其要害的。王廷相是在对程朱理学的心性论的批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性论不断地得到展开,形成了以“性与气相资”为核心的心性论体系。
二、性有善恶之杂
人性的善恶问题是中国古代心性之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秦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还有告子的性无善恶论,等等。汉代出现了性有善有恶论。王充认为,性有善有恶论源于战国时期的世硕。他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论衡·本性》。他自己也认为,“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论衡·率性》。)。在他之前,董仲舒、扬雄也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春秋繁露·玉杯》。扬雄则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与性有善有恶论相近。宋代理学家大都主性善论。张载认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程颢、程颐认为:“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认为,人有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他说:“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而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专指理,故无不善;气质之性,则是由于气禀的不同而为善或恶。“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是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王廷相否认有所谓超然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以气言性,因而也否认了性善论,而主张性有善恶之杂。
(一)气之清浊与性之善恶
以气禀言人性可追溯至东汉的王充。他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而贱。”《论衡·命义》。二程在肯定性善说的同时,对人的不善的原因也作了说明:“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二程遗书》卷一。)又说:“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对此作进一步发挥,认为“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蚀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王廷相沿着前人的以气禀言人性善恶的模式往前进一步发展。王廷相说:
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禀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故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气之生理,一本之道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首先,王廷相以“性与气相资”的观点,抛弃了程朱所谓超乎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的说法,同时也就否定了以本然之性言人性无不善的观点,而直接以气言性,以气禀言人性之善恶。
其次,王廷相在以气禀言人性之善恶时,吸取了朱熹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的观点,用气有清浊粹驳解释人性的善恶。“圣人之形气纯粹,故其性无不善耳;众人形气驳杂,故其性多不善耳,此性之大体如此。”《雅述》上篇。正是因为气有清浊而使性有善恶,有上智下愚之分。
因此,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王廷相提出“性之善与不善,人皆具之”《雅述》上篇。的观点,认为“善固性也,恶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性辩》。)。人性有善有恶都出自人心,都由气禀所决定。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谓之至善,何所据而论?既形之后,方有所谓性矣,谓恶非性具,何所从而来?程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得之矣。《慎言·问成性》。
天之气有善有恶,观四时风雨、霾雾、霜雹之会,与夫寒暑、毒厉、瘴疫之偏,可睹矣。况人之生,本于父母精血之辏,与天地之气又隔一层。世儒曰:“人禀天气,故有善而无恶。”近于不知本始。《雅述》上篇。
由于人性禀受于气,而由天地之气所化生的自然现象亦有善有恶,何况人性?
王廷相提出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是对宋代理学家心性论的发展。王廷相在解释人性有善时,并不依张载的因人禀太虚之气而为善的说法,以为气有清浊粹驳之分,因禀受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实际上否定了张载的天地之性的说法。同时,王廷相也不依程朱的以“性即理”解释性善说,而采用程朱的气禀说。但是,王廷相以气禀言人性的善恶与张载、程朱的性善论一样,都把性看作是天赋的、命定的,因而未能突破宋代理学心性论的樊篱。
(二)对性善说的评析
王廷相以气言人性,并以气有清浊推出人性有善有恶,这与孟子的性善说以及程朱理学的性善说发生矛盾。为此,王廷相对以往的性善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以树立自己的心性论。
王廷相所批评的性善说只是指宋儒的性善说,而对于孟子的性善说,他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王廷相认为孟子言性善仅是指“性之正者”。王廷相说:
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常不在。观其言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亦以此性为非,岂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与不善,人皆具之矣。《雅述》上篇。
王廷相认为,孟子既言性善,言性之正者,也言性不善,言不正之性。“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雅述》上篇。另一方面,王廷相认为孟子言性善旨在修道立教,有治政的作用。王廷相说:
人生禀不齐,性有善否,道有是非,各任其性行之,不足以平治天下,故圣人忧之,修道以立教,而为生民准。使善者有所持循而入,不善者有所惩戒而变,此裁成辅相之大猷也。《雅述》上篇。
人之生也,性禀不齐,圣人取其性之善者以立教,而后善恶准焉。故循其教而行者,皆天性之至善也。《慎言·问成性》。
这样,王廷相实际上调和了他的性有善恶之杂与孟子性善说之间的矛盾,具有折衷的性质。同时,王廷相也将孟子的性善论与宋儒的性善论区别开来。可见,王廷相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宋儒的心性论。
对于宋儒的性善论,王廷相给予严厉的批评。
首先,王廷相认为,宋儒的性善说有悖于孔子的心性论,不符合圣教传统。王廷相说:
昔者仲尼论性,固已备至而无遗矣,乃孟子则舍之而言善。宋儒参伍人性而不合,乃复标本然之论于气质之上,遂使孔子之言视孟子反为疏漏,岂不畔于圣人之中正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儒者不重圣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论与孔子言性背驰与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于圣门,是弃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独以性善为名,何哉?《雅述》上篇。
王廷相认为,宋儒所言性善说实际上是“畔于圣人之中正”,“与孔子之言性背驰”,因此不能起到修道立教的作用。
其次,王廷相认为,宋儒的性善说不同于孟子之言性善,而只是对孟子性善说的牵强附会。孟子既言性之正者也言不正之性,而“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论,而遗其所谓不正之说,岂非惑乎?意虽尊信孟子,不知反为孟子所累”(《雅述》上篇。)。认为宋儒的性善说只是片面地夸大孟子之言性善,而弃孟子之言不正之性。
再次,王廷相用事实批评性善说。他说:
自世之人观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昭昭虽勉于德行,而惰于冥冥者不可胜计。读书知道者犹知廉耻而不为非,其余嗜利小人,行奸侥幸而无所不为矣。故谓人心皆善者,非圣人大观真实之论,而宋儒极力论赞,以号召乎天下,惑矣。《雅述》上篇。
在这里,王廷相以世之人是善者少、恶者多对性善说进行批评,这就说明宋儒的性善说是无事实根据的。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若曰人性皆善而无恶,圣人岂不能如老、庄守清净任自然乎?何苦于谆谆修道以垂训?宋儒寡精鉴,昧神解,梏于性善之说而不知辩,世儒又复持守旧辙,曲为论赞,岂不大误后世?《雅述》上篇。
人性的善恶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经久不衰且终无答案的问题。但是,诚如王廷相所言,孟子的性善说旨在修道立教。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性善说者,或是性恶说者,或性有善有恶论者,其目的都在于修道立教,只是在对修道立教的解释上有所不同罢了。
(三)人之性成于习
王廷相认为,人因气禀的清浊不同而有性的善恶之分,但是,“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无教则不能成”(《雅述》上篇。)。人有善性恶性是由于气禀所决定的,但是否能成性,得视后天的教化。他说:
敦于教者,人之善者也;戾于教者,人之恶者也。为恶之才能,善者亦具之;为善之才能,恶者亦具之。然而不为者,一习于名教,一循乎情欲也。夫性之善者,固不俟乎教而治矣;其性之恶者,方其未有教也,各任其情以为爱憎,由之相戕相贼胥此以出,世道恶乎治!《慎言·问成性》。
在王廷相看来,人无论禀清气或浊气,无论是善性或恶性,关键在于是否能接受后天的教化。“循其教而行者,皆天性之至善也。”《慎言·问成性》。相反,“循乎情欲”,违于教化者,则成恶性。他还明确地说:
人之生也,使无圣人修道之教,君子变质之学,而惟循其性焉,则礼乐之节无闻,伦义之宜罔知,虽禀上智之资,亦寡陋而无能矣,况其下者乎?《雅述》上篇。
这就是说,禀受清气而为性善者,若无圣人修道之教,亦不能成性。这里特别强调圣人的修道之教,重视后天教育。王廷相又说:
善人虽资性美好,若不循守圣人已行之迹,亦不能入圣人之室,言人当贵学也。《雅述》上篇。
他认为,资性美好的性善者还必须重视后天的学习,才能“入圣人之室”。至于禀受浊气的性恶者,更应该通过后天的教育变化气质。王廷相说:
性果出于气质,其得浊驳而生者,自禀夫为恶之具,非天与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谓性。”然缘教而修,亦可变其气质而为善,苟习于恶,方与善日远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王廷相认为,人的本性虽为天赋,但又是可以变化的;禀受浊气而为性恶者,只要“缘教而修”,不习于恶,就可以变化气质而为善。因此,王廷相进一步说:
凡人之性成于习,圣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风以善为归,以恶为禁。《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学校之礼乐,官府之刑法,皆圣人修道之具也。故囿于中者,则变其性而移其习,由之为善则安,为恶则愧。《雅述》上篇。
在这里,王廷相明确提出人的本性可以变化,“人之性成于习”。
王廷相的“人之性成于习”的观点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这一命题旨在说明人性本无大的差别,差别产生于后天的“习”。对这一命题,朱熹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程朱都认为,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中的“性”是指气质之性,而非指本然之性。王廷相则否定有所谓超然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而以气质言性,并从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出发继承发挥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提出“人之性成于习”的命题。
根据这一命题,王廷相对人在性格、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作出解释。对于古人与今人的天赋与差异问题,王廷相说:
天赋相近,何太远哉?习性之日殊尔。古也朴,今也日文;古也直,今也日巧。神凿而灵散也久矣,鸟巢之卵,焉得探而取之?“六经”之教救其习之日降而已矣。《慎言·问成性》。
这就是说,古人与今人的差异是习性上的差异,“六经”的教化只是对“习”的补救。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的差异,王廷相解释说:
东极之民侥,南极之民谲,西极之民戾,北极之民悍,中土之民和,非民性殊于四极也,习于圣人之教然也。蛮夷者,封疆土俗限之也;圣人之教可达,孰谓异吾民哉?《慎言·小宗》。
王廷相认为,各地区的人的本性并非相殊,差异在于“习”,在于是否有圣人之教。这里的“习”当然包括不同时代的社会影响。
王廷相提出“人之性成于习”的观点,强调后天的“习”对于人的影响,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仍言人性因气禀而有善有恶;在性与习的关系上,他认为,由于习的缘故,性善者可成善者亦可成恶者,性不善者可成恶者亦可成善者,正所谓“气之驳浊固有之,教与法行,亦可以善,非定论也。世有聪明和粹而为不道者多矣。”《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性辩》。这里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本性问题。
三、心统性情
王廷相的心性论在言及“心”这一范畴时,特别强调从动态上理解,强调心与情的相互关系。王廷相说:
心有以本体言者,“心之官则思”与夫“心统性情”是也;有以运用言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与夫“收其放心”是也。
智觉者心之用,虚灵者心之体,故心无窒塞则随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觉。是觉者智之原,而思虑察处以合乎道者,智之德也。《雅述》上篇。
在王廷相看来,心之本体即是虚灵之气,而心之用即是知觉。知觉与外界接触,即动之于情。
至于心与性、情的区别,王廷相说:
大率心与性情,其景象定位亦自别,说心便沾形体景象,说性便沾人生虚灵景象,说情便沾应物于外景象,位虽不同,其实一贯之道也。《雅述》上篇。
在王廷相看来,心、性、情同为一体,心是包含性的有形体,情是心之动。在心、性、情的关系问题上,宋代张载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性为虚与气的统一,心为性与知觉的统一。程颐对此作进一步解释:“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王廷相在心、性、情的关系问题上,除认为性为虚灵之气而与程颐所谓性即天理的说法有根本的不同外,其余的方面均与程颐所言相一致;同时,王廷相关于性为虚灵之气的说法正是对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挥。
在解释心、性、情三者的联系上,张载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他说:“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张载集·性理拾遗》。认为心包括性、情。而在张载之前孟子已经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认为性、情都是心所固有。朱熹发挥张载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谓“横渠心统性情之说甚善,性是静,情是动,心则兼动静而言,或指体,或指用,随人所看”(《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王廷相继承张载的“心统性情”的思想,他说:
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横渠理气辩》。
王廷相认为,圣人之性是此心虚灵所具,而为七情所自发。就是说,心包含有性、情,并且心的知觉运动发出性与情,心统性情。
《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中所涉及未发、已发问题也是宋明理学家的心性论所讨论的问题。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情;未发为中,发而中节为和。
王廷相则认为,《中庸》所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在圣人则然,在愚人则不能然”。《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其是言君子平时有存养慎独之功,故未发而能中尔,非通论众人皆是如此的。王廷相说:
夫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惟圣人履道达顺,允执厥中,涵养精一,是以此心未发之时,一中自如,及其应事,无不中节矣。其余贤不肖、智愚,非太过则不及,虽积学累业,尚不能一有所得于中,安得先此未发而能中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
王廷相认为,喜怒哀乐,未发而能中,已发而能中节,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其他众人则是不可能做到的。王廷相进一步论证说:
夫心性之于应事,如形之影,声之响,有诸此必见于彼矣。众人未发而能中,宜皆发而中节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其哀,乐淫其乐,发不中节者常千百乎?时有一二中节者,非天之赋性中和,必素达养性之学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顷,而内外心迹辄尔顿异,不相关涉如此乎?圣人又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雅述》下篇。
王廷相认为,若说人心未发,皆有天然之中,何至应事便至迷瞀偏奇?此则体用支离,内外心迹判然不照,非理之所固有。“君子能尽存养省察之功,则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可谓之中,似亦理得;不然,通圣愚而论之,则其理不通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廷相从性有善有恶出发,认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只是对圣人而言,而其他人则未发不能谓中,已发不能中节,因而需要圣人教化以致中和。
人心与道心是宋明理学家的心性论所讨论的问题之一。人心、道心的提法始见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将此十六字与道统说结合在一起,而称之为“十六字心传”。而在朱熹之前,二程已开始讲人心、道心,谓“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二程遗书》卷二十四。朱熹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此道心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王廷相说:
谓之人心者,自其情欲之发言之也;谓之道心者,自其道德之发言之也。二者,人性所必具者。《雅述》上篇。
恻隐之心,怵惕于情之可怛;羞恶之心,泚颡于事之可愧,孟子良心之端也,即舜之道心也。“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嗅,四肢之于安逸”,孟子天性之欲也,即舜之人心也。由是观之,二者圣愚之所同赋也。《慎言·问成性》。
王廷相认为,人心、道心均为人所具有,且“圣愚之所同赋也”。他还明确地说:“人心、道心,皆天赋也。”《慎言·御民》。又说:
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与生而固有,观夫虎之负子,鸟之反哺,鸡之呼食,豺之祭兽,可知矣。道化既立,我固知民之多夫道心也。人心亦与生而恒存,观夫饮食男女,人所同欲,贫贱夭病,人所同恶,可知矣。《慎言·问成性》。
对于“十六字心传”,王廷相说:
道心非气禀清明者则不能全,故曰“道心惟微”,言此心甚微眇而发见不多也;人心则循情逐物,易于流荡,故曰“惟危”,言此心动以人欲,多致凶咎也。人能加精一执中之功,使道心虽微,扩充其端而日长;人心虽危,择其可者行之而日安,则动无不善,圣贤之域可驯致。①
王廷相认为,心之本体是虚灵之气,而道心本于所禀清明之气,所以精微而“发见不多”,但可以加以扩充而“日长”。人心则是所禀浊驳之气,如果随人心而动,则人欲横流,“多致凶咎”。他说:“人惟循人心而行,则智者、力者、众者,无不得其欲矣;愚而寡弱者,必困穷不遂者矣。岂惟是哉?循而遂之,灭天性,亡愧耻,恣杀害,与禽兽等矣。”《雅述》上篇。所以“惟危”。但是,可以通过“精一执中之功”,在使道心得到扩充的同时,择人心中合理的方面而动,这样就可以进入“圣贤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