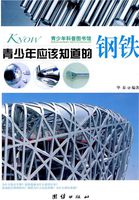为了偿还债务,我非常辛苦地工作。我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商人、计算数字的高手,并精通多国语言。父亲和叔父派我到海外考察他们的分支账房。因此,我才会来到位于南海另一端的巴萨尔达——日升帝国的诸多大城之一。沙漠之中,大批骆驼商队在这个国家来来往往。我们在这里买布匹、织毯、乳香和樟木,用船只运送到寒冷的北方城市。卡德连姆苏丹颁布了一道旨令,准许外国商家在当地投资;于是,不久之前,我们家在此开设了一家商队驿站。第一晚,我走到平台上。漆黑如矿的夜幕上,点缀着闪烁繁星,下方的城市铺展延伸,线条错综复杂,以广场上曲线优雅的圆顶间隔。夜晚的气息仍有晴天朗日的芬芳,茉莉的香味弥漫在各花园的幽暗角落。围墙后方的棕榈树下,一条明亮的小径沿河蜿蜒,消失于丘陵之间。第二天,我写信禀告父亲,希望留在此地发展。那一年,时值我25岁,原本并没有打算滞留两年以上。而且,根据父亲和叔父商量的结果,在那之后,我也应该要回国掌管整个家族的事业。
驿站的位置很理想,就位于城门口,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意。于是我扩建前庭,增加客房的数量,清扫马厩,挖深水井,聘请了一位厨师和一位理发师……但这一切却有去无回,全数赔光。那些徒步小贩,以及那些鞋底从没离开过沙漠、永远不喊累的商队领路人,他们宁愿到较远的地方投宿,却拒绝在外国人经营的铺子过夜。
我不认识任何人,但至少知道一件事:无论来自灰暗阴郁的北方,还是阳光充足的东方,买卖议价的艺术都全凭一张嘴;然而,这些小贩却都热衷于“拿斯赌”。那是一种类似下棋的赌博,玩法也是在棋盘上移动象牙棋,差别在于观棋者可以介入,并依据每一次得分下注。在赌局中,话语的确扮演了某种角色,重要性却远不如沉默、眼神、姿势、胃口,以及衣着打扮所传递的讯息。倘若耳朵太迷糊,眼睛太昏沉,只要一手棋翻盘的时间,钱就会全数赔尽。我每晚都到市集拱廊下注几把。在那里,我才真正学到经营之道。绝对不可一战论成败,要懂得以退为进。我胆子够大,运气够好。无论输或赢,必定在市集找家餐厅,邀赌伴们同桌吃喝一整晚。渐渐地,就这么破除了他们对我的不信任。这群朋友喊我科尔内利斯·贝。他们讲各种故事给我听,关于路上的风险和意外,有的恐怖惊人,有的神奇奥妙。对他们来说,一名真正的商人不能守成等待财富降临,必须永远不断地主动前往冒险。所有人都鼓励我出发,要我也在大漠的金沙里留下足迹。
我买了十几只足行鸟。那是一种强壮且耐力极佳的禽类,但必须经过许多训练,才能驯服它们。出发进行第一趟旅行时,我加入一支骆驼商队,他们的目的地是胡嘎里山,需朝东北方行走35天。到了那里,可轻易将红胡椒卖给各山寨大王,还可以做些兵器的买卖,只要用精钢炼成,长矛短刃他们都收。旅行途中,我见识到“呼噜祖风”的威力。这种风吹得人皮开肉绽,牲畜流泪哀鸣。整整三天三夜,我蜷缩在蹲趴下来的坐骑鸟后方等待;尽管戴了面罩,脸孔仍遭细沙狠狠鞭打,鼻孔堵塞,耳朵受尽蹂躏。沙尘暴狂扫肆虐,天色昏蒙暗红,不时劈下骇人的闪电。风暴终于过去之后,我发现雷火将沙粒烧成细碎的玻璃,处处留下“之”字形的曲折痕迹。我因为太用力紧抓毛毯铺盖,掉了三片指甲:左手两片以及右手大拇指上那一片。但因为当初在这趟旅程上所下的赌注,对方加了好几倍报偿给我。商队的伙伴们也都做了几笔好买卖,因此,回程的气氛颇为欢乐。有一位伙伴跟我一样,也是布商。他知道当地所有的布料种类,特别喜欢质地轻软的料子,采买的对象多达三十几名织布工匠。他听说过云绸,但认为那只不过是空泛的传说。他说服我陪他去沙漠另一端——亚马逊女战士国的入口。他拿在不期市集上所能赚取的大笔财富诱惑我。我们决定一起前往。
我写信告诉父亲:我必须在日升帝国多滞留一年。
“不期市集”这个名称的由来,在于人们无法确切预测市集何时会举办,也根本不可能事先知道地点。于是,商人们派出探子,一个绿洲一个绿洲地侦测调查。这些探子真不愧为沙漠之鸟。他们低调地栖息某处,凝听,撷取两三项情报,拔营,前往他处栖息,获取另外两项情报,却与先前打听到的互相矛盾。他们抱着谣言又满怀希望,再度出发。他们不断旅行,焦急难耐,难以入眠,交由星辰或骰子来决定方位,然后继续往更远的地方飞。因为他们感觉到亚马逊女战士即将抵达。最聪敏的探子能比其他人早几天预测出结果。在他们所选中的城市里,突然万头攒动,人潮仿佛凭空涌出,蔓延到每一条大街小巷。商人们躁动难耐,到处都爆发争吵,甚至引发刀刃出鞘。野狗在花园深处打斗,深夜里也能听见它们的呜咽声;特别是几只身上带有火焰斑马纹的,绝不能接触到它们的目光。
如果探子们的判断正确,气宇轩昂的女战士会在东方鱼肚白时分进城,带来无比光滑柔软的皮草,其中甚至有最令人垂涎的蓝狼皮。女战士们想要的是丝绸纱罗、琥珀、小贝壳、没药,以及青金琉璃。她们拒绝任何以金属铸造的货币。此外,她们也不说话。人们放下商品,等待评价从她们的双唇发落。一声“叱咤!”颤动,可能表示好,也可能是坏,端看她们是否同时用一只黑箭的羽毛尾端触碰商品。交易持续一整天,皮草的市值根据她们对商人提供的珍稀货物的青睐程度而定,任何规章或评判都不能左右她们对货物的迷恋或轻蔑。
女战士们在日落时分离开,消失在沙漠里,直到不能再远,人们才听见她们的歌声:一阵壮阔的低吟,宛如夜里落雨,淅沥蔓延。许多人跋涉至此,只为听远方传来的回响,任自己在这比鸟啼更婉转,比风吟林间更优美的歌声中卸下武装。
不期市集的奇幻色彩吸引各路人马散播消息,有的好,有的坏,但大部分是无法证实的捕风捉影。
就在这儿,就着眼下的一盘杏仁果和一杯茶,我再次听人说起云绸。那人把这布料夸赞得天花乱坠,面对在座众人狐疑的撇嘴和同情的微笑,愈讲愈激动。我加入听众所围成的圈子。
“它当然存在。”他大声嚷着,“大家都听过那种生活在树林里的奇怪蜥蜴,它们会根据躲藏的环境改变身上的颜色。这种薄纱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它的纤维能捕捉白天或夜晚的光线。”
“那么,你倒说说:这般神奇的东西要上哪里去找?”
“翠玉国。”
“都朗,你这人还真好骗!蜥蜴会隐身,这还说得过去,但布料怎么可能会捕捉天空的颜色?!”
“你把我当成骗子?”
“不,不是骗子,但说你是个傻子,这可没错!……那个国家远得要命,关于那里的传言,从没有人亲自去当地证实过。一块根本没人看见过的布料,你为什么相信它竟然存在?”
我拿出魄力介入谈话。
“云绸,它的确存在。”
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我朝那位都朗走去。我曾听说他是一位极为优秀的商队领路人。
“我曾亲眼见过。”我继续说。
“谢谢你出言相挺。很高兴遇到一个不沉溺于无知自满的人。”
“但是我所看到的云绸并非来自那个地方。你说的翠玉国位于哪里?”
“东方。非常远。避开冬季的话,至少要走六到八个月。”
“那是不是一个圆形的大国,中央有一座蓝色的山?”
听我这么一问,在场所有人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啊,是啊,要这么说的话,那里确实有很多山,高耸无比。也正因如此,难以找到从那里生还的人。那些山脉可说是无法横越。但不是蓝色的,应该说是白色的,因为山顶万年积雪不化。但是不横渡这些山不行,因为那是抵达翠玉国的唯一方式。”
“你认识路吗?”
“我没办法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告诉你。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想探路,打算付我多少钱买情报?”
“一毛也不付。”
他转开头,要大家见证这些北方商人有多荒谬。
“不过,要是你答应带我去……”我继续说。
我说出的数字之庞大,令他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听众的圈子朝我们靠拢。
“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有兴趣,”我的语气坚决,“我打算在明年带领一支商队。我要带这队人马横渡那些山脉,无论山有多高。我要找出通往翠玉国的通道。我需要牲口、粮食和身经百战的英勇伙伴。倘若运气和神明与我同在,我将带回足够给全城人做衣裳的云绸,跟我一起冒险的都能发大财。谁愿意加入?”
商人们犹豫着。尽管这笔生意听起来令人血脉偾张,却没有人会为了那样一个荒唐不切实际的幻想,投下这么大一笔赌注;除非他是笨蛋或是疯子。
然而,其中还是有两个人举手。第一个人,大家都认识,名叫康比斯,是贝朵安部族一位备受敬重、认真严肃的老师傅,负责在商队中牵牲口行走。他将手放在额前和胸口上,前来给我一个正式的拥抱礼。他的年纪应该长我不止一倍。第二个人只对我点头致意,一句话也没说,随即悄悄退出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