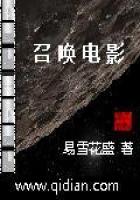回到巴萨尔达之后,我写信告诉父亲:我必须至少再多待两年。我雇用了都朗,派他招募人手,采买牲口和器材。康比斯带来半数资金,我们不愁粮食不足。在进行准备工作的这段时间,第二名自愿加入的商人一次也没出现。
我对于要走的路线一点概念也没有。在这整个地区,找不到几张地图;只能靠老师傅们冗长的回忆来补充。不过,这里住着一位地理学者,慕苏丹之名而来,正在编写一部诸国论著。我前去拜访。他在我面前展开好几卷上古时代的羊皮纸,在这些羊皮纸上呈现翠玉国的方式有千百种,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从中勾勒出较精确的想法。这真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过,他倒是对一幅自己绘制的地图十分得意,这幅地图画的是日升帝国及其边境。他把地图摊开在桌面上,食指放在地图中央一座大城的图案上。
“这里是锡兰答内,日升帝国最东之城。”
他的手指向右滑动,移到地图另一端。
“而这里是喀拉古伊,把守白色山脉各隘口的重镇。翠玉国尚在此城之外,在那些山脉后面,往旭日升起的方向再过去。从锡兰答内到喀拉古伊,您有两条路线可选。较保险的一条要朝东南方绕一个大圈,经由乳白海,直到勒奇思港。接下来,沿着灰河回溯向上,然后斜偏往喀拉古伊。这趟行程很长,要停驻许多站,在那些地方都能安全做买卖。另外一条路线则从锡兰答内出发,走直线到喀拉古伊,穿越大小沙漠、盐海以及石族的国度。”
“这条路比较短。”我点出两者之不同。
“但我不建议您走这条。”
“为什么?”
“太危险。这条路早已没人走。”
我向地理学者打听翠玉国与靛蓝双岛之间是否有关联。他要我把岛名再说一次,然后表示对这个名称毫无印象。我把伊本·布拉扎丁的著作拿给他看。他撇撇嘴,说他从没听说过欧赫贝岛。我不死心地解释:“这座岛位于地球的另一面,幅员广大,伊本·布拉扎丁就来自那个地方。他的书里都有记载,但应该还能找到别的证据,例如海岸探勘的数据,或某些远行至此的航海家曾记录的见闻。”他摇摇头吸了一下鼻子,带着些许傲慢。我认为地球可能是圆的想法把他嘴角那一丝宽容的微笑也扯下了。
“怎么连您这样知书达礼的人也会相信这种蠢话?我们脚下有一座大岛?难道那里永远不下雨,人们走路头下脚上吗?”
我只能道谢感激他的协助。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们的沙漠商队离开巴萨尔达。一个月后,抵达锡兰答内。这座大城处处雪松成荫,花园环绕。我们的人马暂时解散,各自前往大城的不同角落:好几名徒步小贩有亲人在此。我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聚集大家商讨意见。都朗选择南边的保守路线。康比斯虽然年纪较长,却完全听不进去都朗的建议:
“我带领商队前往勒奇思不下15次。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荷包也赚饱了。我加入这支商队,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沙漠之路探险。”
“康比斯说得对!”暗影中响起一个声音。
我们一致转过头去。第三位商队老板走近前来,用大漠可汗的姿势弯腰行礼。
“我是木席靼勒部族的伊德里思汗,在锡兰答内出生长大,所以宁愿在此等各位到来。我的商队已经准备好了,这会儿,我的马夫们正把牲口牵来加入你们,我也带了粮食与诸位共享。我知道沙漠这条路,的确很危险,但真的快多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运气,通过红花迷阵就没事了。”
“一点运气?”都朗尖酸讽刺,“去问问那些没能回来的人吧!”
我对他投以疑惑的目光。
“红花迷阵,”都朗接下去说明,“是盐海和石族国之间一道极为棘手的谷地。若在适当的季节前往,没有任何危险:树林正值睡眠期。但若遇上屠杀季,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树木醒过来后会长满尖刺,射出千万飞针,如野猪獠牙一般又尖又长,力道强劲恐怖,没有任何活物躲得过。”
“很好,”我说,“只要在适当的季节出发就行了。”
“可惜你无法预测那个季节何时到来。事实上,何时展开屠杀季,由树木本身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就没有任何庇护的方式?”
“这些树木会射杀方圆30步内所有会动的东西。蜷缩在坐骑的腿肘下,把头埋进它们的蹄子下,通通没有用。人与畜,每一个活口,最后都将在尖刺针雨之下结束生命,活生生变成插满针的针包。据称,森林汲取遍地鲜血,制造新的树液。拜托别算上我这一份。”
“不过,只要晓得这件事就行了:在屠杀季时,森林会开满壮丽的红花。”伊德里思汗带着饶富兴味的微笑,断下结论,“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
“那么,我想,该是大家去休息的时候了。”
加上伊德里思汗的人马,商队人数多达60人,牲口也增加一倍。我们步行了三个星期,走过一座又一座绿洲。真正的沙漠从盐海边才算开始。地平线后方,海面强光粼粼,闪得人睁不开眼。白日之中,酷热直逼难以忍受的极限。从第一天起,盐分就吸干了我们的唾液,炙烤我们的肌肤,刺激我们的眼睛,攻击牲口的脚皮。都朗建议我们牵紧它们,以防它们误以为那一大片银白闪亮的是湖水,拔腿冲过去。那一面面镶着细沫的银镜与天空较劲,不甘示弱地反射强烈光线,但其实下方暗藏流沙。在这片沙漠里,所谓的路,不过就是因覆盖了一层厚盐而变硬的狭长沙洲。碍于日间的耀眼亮光,这些路径不易察觉;但到了夜晚,无数萤火虫栖停其上,描绘出一整张纵横交错的路网。
所以,我们只在夜间行走,跟随地上隐隐闪烁的微弱星光前进。商队人马踏过,碾碎小虫,逐渐将路径一条条踩熄。而商队队伍拖得过长,走在最后的几人就少了这点点微光指引脚步。康比斯的一名马夫因而迷途,滑入一片浓缩盐卤,还把用缰绳牵着走的三头牲口一起拖下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搭救,他们仍一下子就被吞噬;而队伍最前方,领路人都朗高声催促我们加快脚步。第七晚,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指示我们:铁矿山已在附近。那差不多是沙漠的中心点。根据传说,铁矿山下埋葬了一整支军队。而事实上,的确有一种闷闷的战鼓擂鸣从地面传出,在无边寂静中,音场显得更加清晰。都朗强制规定我们以最隐秘的方式行动,以免惊醒这支沉睡军队。伊德里思汗熟知这些山脉的每一个细节,反而坚持绕道前往,保证在那里步行不需害怕突然陷入流沙,而且找到水源的几率也很大。他说得果然没错。尽管山势险峻不友善,总算也提供了些许凉荫,甚至有足够的水,让我们补满库存。
伊德里思汗是位神秘的男子。与许多木席靼勒人一样,看上去有一股傲气。他蓄着精心修剪的短须,眼神锐利,动作精准,话不多。疲累似乎永远无从对他下手。只要一壶水,一把椰枣,再带上猎兔犬卡伊,他就能在黎明前出发狩猎,几个小时之后再追上我们,且仍然神采奕奕;反观我们被夕阳拉长的影子显得无精打采,似乎把我们拖在更后面。伊德里思汗用他那简洁有力的点头方式向我打招呼,归队回到他的位置。
越过铁矿山之后,盐海又夺走我们两匹牲口,还灼瞎了一名老马夫。我们抵达盐海边缘的山丘,宛如船难历劫生还者,皮肤红肿疼痛碰不得,精疲力竭,全身脱水消瘦。距离喀拉古伊,路途仍十分遥远,我们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到达。
红花谷那些大名鼎鼎的夺命树看起来并不像具有攻击性。一株株大树笔直抽高,树叶稀少;但远远望去,树干与树干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近,进而形成一座浓密阴森的柱廊。一小群珠鸡从我们脚边经过,一路咯咯叫。伊德里思汗跳下坐骑,一手抓住猎兔犬的项圈,另一手提着一只布袋。这几天以来,我一直对那只布袋里时不时的跳动感到好奇。他一下子把袋口打开。一只沙漠野兔从中跃出,用后腿蹲站,眼睛眨动,长耳轻摇,跳了几十步之后,逃逸无踪。伊德里思汗等了一会儿,然后才放手让猎兔犬去追踪野兔。犬儿消失在夺命树林间。我听了好一阵子,林子里的吠声逐渐弱不可闻。我们再度被无边寂静笼罩。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伊德里思汗呼喊他的猎兔犬。一次,两次,十次。传来一声哀嚎回应,猎兔犬卡伊总算回来了。它气喘吁吁地在主人脚边趴下,背脊剧烈起伏,被划开一道好长的伤口。伊德里思汗弯腰检视它的伤口,想必是擦掠树刺所致。依他判断,这反而是个好征兆,因为如果被触碰到的那棵树做出骇人的反应,其他树木必然随之跟进,那么狗儿早该被万箭穿心。他撕下一条布,包裹猎兔犬的腹部,示意我们往前。
我们战战兢兢地走入林地,不敢发出一点声响,试探每一寸土地。森林愈来愈茂密,小径蜿蜒,鸟鸣回荡。想象不出比这里更安静的地方。尤其是那片树荫,让人感到十分舒服。恐惧远离,康比斯和我甚至开玩笑说这些故事都是刻意编来吓小孩的。就在我们放肆大笑之时,骇然惊见白骨成堆:有一整支沙漠商队来不及逃离便被原地钉死;稍远一些,又见另一队人马,在同样的状态下被射杀个措手不及。于是我们重拾初踏入林时的谦卑态度。事实证明,这座森林里,每走几步就是一堆刺满植物利箭的白骨,叫人不禁觉得自己正走入一个张大嘴巴等着吃人的陷阱里。不过,最让我们恼恨的是喉头干渴发紧,脖颈之间汗流不止。走出迷阵后,我们整个松懈下来,欢天喜地地攀登一列山脉。山里常见羊群放牧,但牧羊人应该不常见到活人走出那片森林。他们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我们经过,仿佛我们是一群直接从地狱逃出来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