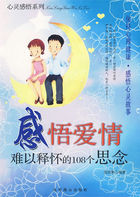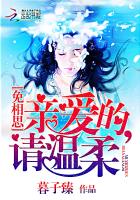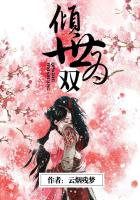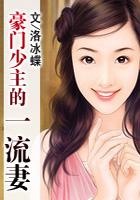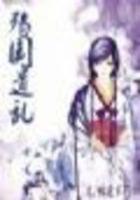这部书,并非什么善珍版,是当时的普通坊间本,但时至今日,叙上一叙,也是“版本史”上的掌故了:书是精装上下册,洋纸,绿布皮,题名为“绣像增评石头记”。扉页背面,两行字是“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又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京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我因此想:乾隆辛亥“程甲本”刚印出,两年后就从浙江出口传到了日本的长崎。看来日本人如今还出红学家,这事不为稀奇了,-这应该叫作日本版吗?上面又一个日本字无有。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光绪本翻版,即坊间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汇在一起的)之本。
这绝不能算是“珍本”、“秘籍”,但它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深厚感情,我题记过,手装过,几历沧桑之变,现时还存有上册半部书,已是缺帙残编,弥觉有青毡敝帚之感。
“日本版石头记”,在红楼版本史上是晚近之品,然而屈指算来,也是将及九十年的古物了,令人憬然慨然。以后我上初中时(上的是天津河北中山公园内的觉民中学),上海忽然兴起了一阵出版奇风:用报纸“平民化”的规格印制了一大批通俗文学、笔记、野史、诗词古文等传统流行读物,标价很贵,可实售打“一折八扣”,便宜得出奇,印及数量又大,我和家兄祜昌,有一回在“大胡同”(天津著名地点,有好书店)选购《红楼梦》“善本”,就取了一部“大达”版的(当时这种书有新文化、启智、大达……等书局版),四册,牛皮纸封面,携之而归,以为至乐。-这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寒碜的“治红”历史,实堪齿冷。
寒碜,是人家齿冷的原由之一,之二呢,还由于和胡适打了交道。
和胡先生打交道,倒一点儿也不是因我异想天开,妄欲攀附令名盛誉。那是因为我在祜昌的提示下,发现了《懋斋诗钞》,他主动与我打交道。我那时是一纯书呆(如现在的还是这样子),丝毫不懂得这是一种荣耀。记得有一位臭架十足、从不俯垂贵目、未交一语之人,忽然向我打招呼赐以谬奖,我还糊里糊涂,很觉纳闷。
正因我的这书呆气甚为严重,我才真的“异想天开”起来,我竟然提出向他借用世上唯一的无价之宝《甲戌本》。其实,彼时我也意识不到那书的真价值应该是多少大洋,直到1980年在北美国际红会上,潘重规先生在台湾费了大力气才借到它,携至大会展出,使诸位与会之学者专家,大享眼福,才知道此书飘洋过海,游历美洲,该会是给予了数万美元的保险费方才议妥交付借用一时的-这时我才明白此书若“出让”,一定可以换成一笔很可观的美金。
这样一部书,我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一张口,胡先生就让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给我送到燕京大学来了。而且,此后他一语未再催问过,表现了非同寻常的慷慨的度量与对人的信任。
伴随《甲戌本》同至的,还有一部大字《戚本》,上有胡氏题记,盖有“胡适的书”四字的“白话印”。-不提这书还则罢了,一提起,事情可就大了。
伴随《甲戌本》录副的原委,我在《石头记鉴真》跋尾中有过描叙,此书送还后,大字《戚本》还在我手未及璧返。承陶心如先生惠借我《庚辰本》的照相本(当时原本未出),我便用了80个夜晚工夫,将它的一切异文与批语,详细校录在《戚本》上,连一点一划之别也不放过,粲若列眉。这工夫是在燕大图书馆研究生专用桌位上进行的,用一方祖砚研朱墨。那时梅兰芳先生之令郎绍武君,和他的女友(德国籍)来坐于旁,目击此一情景,绍武便给这位洋妞儿介绍《红楼梦》是为何物。还拿着一部英译本“辅导”。
这部奇特的本子,宣统、民国交替之时石(影)印的,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公开的古钞本,与程高伪本大不相同,但当时(直到后来多少年)也无人认识。《庚辰本》则是我请张伯驹先生访求原书,因那时索价讲黄金多少条,张先生财力不及,因而介绍给燕大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他们收藏了。而此本与《戚本》的影印,都是由《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出版之后才引起的“红潮”,由此可想,那部胡藏周校的《戚本》非同一般书物。
但这部堪称珍本的《石头记》远在“破四旧”之前就遭到了厄运。
因为我与家兄祜昌决意搜集古钞,汇校写定一部真的雪芹的(而不是程高篡改的)《红楼梦》,此珍本与一些别的版本,都由家兄带往天津南郊的老家去,他孜孜不倦进行浩瀚无比、不为人知的苦工力作。这么一来,有人就大起疑心,并实行“告密”-因为那时已经传闻:我们这两书呆与胡适有“来往”。一个大年三十夜,“告密”生效,以致祜昌家被查抄数次,直到片纸不存。那部《戚本》,正好是“与胡适串通”的铁证,因此成了一桩“政治大案”。
浩劫过后,政策逐步落实,我大约不止十次八次地想尽办法反映这一情况,希望将那些珍本《石头记》、《红楼梦》以及祜昌苦作的成果,查明下落,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至今那部《戚本》无有任何部门注意查明下落。我只想说一句:那查抄书是开列清单、有正式手续的,不同于一般“四旧”有散失之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不知被哪位“扣”在他柜子里。此本我们不必据为“私有”,愿捐公家,充作陈列品,供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界人士参观研究,岂不是一件别开生面、饶行意味的“特级文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巡游旧书肆是一大乐事,单是东安市场一处,那真称得上是一座宝山,你绝不会“宝山空入”,旧书古碑之富,标价定值之低,如今想来真比梦境还“玄”,难以置信。最奇的是一种书同时可以有二三部,我就在这“当口儿”上“取巧”:比如一部敝旧得很,价则偏高;一看,又寻着一部,不但十分整洁,而且价目低得很多,于是大喜,买回来,灯下题记,心中大是得意!-一次,忽见小字本《戚本》,完好如新,不是“旧书”,是老货底未售者,价才三元挂零。我亟收一部,后又再收一部送与家兄,记得两人坐故宫茶座上,还为此本题了绝句,以志其事。
再一次,是在国子监书店的“内库”,见有大字《戚本》二部,知其难遇,不避“重复”,也收了一部。谁知这一部也成了“历史文物”: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影印此书,却无处寻求原物,到我处觅借;我将后收的大字本借与他们,拆散成零页,好去影印。印成后,好毛边纸,蓝布函,字迹清楚,质量很高。我的书被拆散了,所得报酬是一部新印的两函,视之,一函“牙签”折断,函不能固封-大约出版社因这样难卖,就拿来酬谢我了。
《己卯本》也影印了,但因有人妄加“处理”,弄得面目全非,令人不验原件,简直不敢凭信和运用。
六十年代初发现的《蒙古王府本》前年也影印了,它的价值袁拙撰序文中曾略及一二。它与《戚本》是姊妹本,有了《蒙府本》,被冷落了数十年的《戚本》的来龙去脉,这才开始得到认识。
1984年12月,雪夜登上飞机前往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冰天雪地,得《红》便暖意有余。我是奉国家委派而往的,我是作为专家去的。单说这个本子,价值极高,中苏联合影印,今亦行世。这真是令人不胜欣幸之事!这个本子的价值,官是低估,反而说我是“高估”。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清,我与祜昌的大汇校《石头记会真》中,显示得斑斑俱在,有目者自能共睹,所以不必认为这又是什么“仁智之见”,“口舌之争”。
四十三年过去了。回想最初,世人连一部真《红楼》也休想看见。当时我就向胡适提出,这是大问题、大事业,一定要全力经营一部真的《红楼梦》才对得起雪芹,对得起中华文化,对得起子孙后代。如今回顾一下,这些珍本已然在陆续影印,真是不禁欣慨交加。种桃自有摘桃人,如是如是。
贩书杂记
魏广洲
我自14岁起,由河北冀县来北京琉璃厂松筠阁旧书店学徒,数十年来结交了不少买书的学者。我从他们那里受到不少教益,学来不少知识。仅就记忆,随手留下片断旧影。
向达教授
向达先生(1890-1966)字觉明,湖南人,土家族。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代表作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问世以来,多次重版。他也被人们誉为敦煌艺术的拓荒者,西域文明的采珠人。约从1953年,他又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一向办事认真的向先生,亲自采访图书以充实馆藏,无论多少书贩送书,他都过目检阅,对送书人说话和蔼,平易近人。每次送去的书都要当时看完,有时看到下午一时多才回家吃午饭。他常说你们从城里骑车跑路数十里,够辛苦的。
我头一次遇见向先生是1932年中秋节,由谢国桢先生介绍认识的。那年我才21岁,在松筠阁学徒满数年了。这天到谢先生家送书账单,碰巧向先生正在那里。松筠阁书店开设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经理刘盛虞。这个书店有一个好传统,对于顾客不是专看“钱”。知道某人研究哪一方面的学问,需要哪些书,我们就登门送书,供其选购。有的当时决定,或者留下考虑,日后再定。不合适则看完退书。有时对方决定要买,而当时手中不便,书款可以记账。每年三节送上书单。如还不能算清,或先付若干,下节再说。
在谢先生家结识了向先生,以后就经常给他送书。他曾经称赞我如同飞鸟似的不停翅膀,一天不定要拜访几户主顾。
七七事变以前,向先生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住景山后街碾儿胡同,我经常到那里去。那个房子分里外院,向先生住里院,外院住的是研究唐史的著名学者贺昌群先生,因此,我又得识贺先生。
建国以后,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海淀燕京大学旧校址,图书馆工作也有发展。在这个时期,向先生经手给北大图书馆买了很多善本古籍和罕见孤本及朝鲜刻本。其中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及《刘随州集》就是我卖给向先生的。1957年琉璃厂书店公私合营前,我去天津收书,在劝业场楼上文物商店遇着曹伯方老先生,他从方药雨家收购梵文贝叶经约二百叶,还带着原来红漆木夹板一副,黄色布包袱一方,我用了一百元买到手的。在火车上越看越高兴。回到北京,即携书骑车奔赴北京大学,向先生一见就决定图书馆可收。当时尚须书业公会议价,但我送到公会,议价人却说:没见过,不懂是什么文字,并说佛经没有人要,不值钱。最后勉强定了一百二十元。向先生学识渊博,买书也有眼光,我是货卖识家,当时就按议价让给了北大图书馆,而向先生温文尔雅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张申府的题字
张申府先生(1893-1986),早年投身五四运动,后在清华、北大任教授,著有《所思》、《所忆》等。解放后,由周恩来总理推荐加入北京图书馆,负责古籍善本书的收购工作。我在贩书时遇到珍贵版本,首先想到卖给国家。例如宋版《礼记释文题跋》一书,原为海源阁杨家藏书中四经四史之一。北京同业将拍此书,我事先与张先生取得联系,最后由我购得,送归北图,终于使杨家旧藏宋版四经四史破镜重圆。
张先生对此时常念及,认为我的做法值得称赞。20年前,张先生曾经给我题字留念,原文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