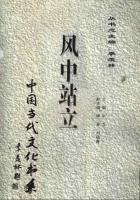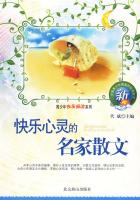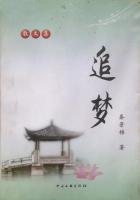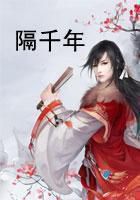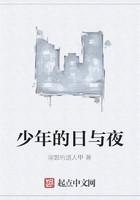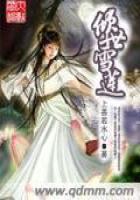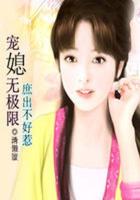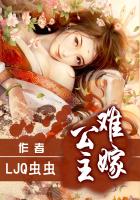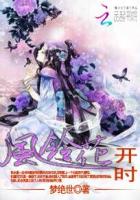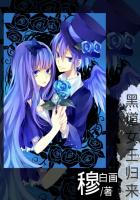人与书
郁达夫
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智识饥渴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出来。
因书本与人类关联之亲密,所以古来学者多把书本当作人类的朋友看待。史曼儿说得好:“一个人常常靠了他所读的书而出名,正像他靠着所交的朋友而出名一样。因为书本和人们一样,也有交谊。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很好的友伴中间,无论是书或是人。”
同时亦有一位,他却把人生当作书本来看,那就是诗人高法莱了,他说:“一个人好像一本书,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笑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卒读者。可是最后的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恕我续上一个“貂尾”,就是在人的诞生之前的受精成孕,就是书版付印前之文人绞汁的草稿了。
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
童年之梦渊蒋建国作冤
书的抒情
柯灵
说到书,我很动感情。因为它给我带来温暖,我对它满怀感激。
书是我的恩师。贫穷剥夺了我童年的幸福,把我关在学校大门的外面,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我,给我以慷慨的哺育。没有书,就没有我的今天。---也许我早就委身于沟壑。书是我的良友。它给我一把金钥匙,诱导我打开浅短的视线,愚昧的头脑,闭塞的心灵。它从不吝惜对我帮助。书是我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再愁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它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我真的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我忙完了,累极了;当我愤怒时,苦恼时,我就想亲近它,因为这是一种绝妙的安抚。
我真愿意成为十足的“书迷”和“书痴”,可惜还不够条件。不知道谁是监狱的始作俑者。剥夺自由,诚然是人世最酷虐的刑法,但如果允许囚人有读书的权利,那还不算是自由的彻底丧失,我对此有惨痛的经验。
对书的焚毁和禁锢,是最大的愚蠢,十足的野蛮,可怕的历史倒退。
当然书本里也有败类,那是瘟疫之神,死亡天使,当与世人共弃之。
作家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亲友,献与读者,是最大的愉快。如果他的书引起共鸣,得到赞美,那就是对他最好的酬谢。
在宁静的环境,悠闲的心情中静静地读书,是人生中最有味的享受。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夜,我曾经避开海洋般的冷漠与白眼,每天到龙华公园读书,拥有自己独立苍茫的世界。这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
书本是太阳、空气、雨露。我不能设想,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书的鉴赏
朱湘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逸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它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昏是婚的古字:在太阳下了山,对面不见人的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擎着红光闪闪的火把,悄悄向一个人家走近。等着到了竹篱柴门之旁的时候,在狗吠声中,趁着门还未闭,一声喊齐拥而入,让新郎从打麦场上挟起惊呼的新娘打马而回。同来的人则抵挡着新娘的父兄,作个不打不成交的亲家。
印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矫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楷体是最常见的了。这里面又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一种是通行的正方体;还有一种是窄长的楷体,棱角最显;一种是扁短的楷体,浑厚颇有古风。还有写的书:或全体楷体,或半楷体,它们不单看来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并且有时有古代的写本,很足以考证今本的印误,以及文字的假借。
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本旧书,则开章第一篇你便将看见许多朱色的印章,有的是雅号,有的是姓名。在这些姓名别名之中,你说不定可以发现古代的收藏家或是名倾一世的文人,那时候你便可以让幻想驰骋于这朱红的方场之中,构成许多缥缈的空中楼阁来。还有那些朱圈,有的圈得豪放,有的圈得森严,你可以就它们的姿态,以及它们的位置,悬想出读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少年,还是老人;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你也能借此揣摩出这主人公的命运: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了人间?是子孙不肖,将它舍弃了?是遭兵逃反,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还是运气不好,家道中衰,自己将它售卖了,来填偿债务,或是支持家庭?书的旧主人是这样。我呢?我这书的今主人呢?他当时对着雕花的端砚,拿起新发的朱笔,在清淡的炉香气息中,圈点这本他心爱的书,那时候,他是决想不到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他自己的未来命运,是个怎样结局的。正如这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我,不能知道我未来的命运将要如何一般。
再进一层,让我们来想象那作书人的命运:他的悲哀,他的失望,无一不自然地流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时候,时而跟着他啼,时而为他扼腕太息。要是,不幸上再加上不幸,遇到秦始皇或是董卓,将他一生心血呕成的文章,一把火烧为乌有;或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一般命运,被浅见者标作禁书,那更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呵!
天下事真是不如意的多。不讲别的,只说书这件东西,它是再与世无争也没有的了,也都要受这种厄运的摧残。至于那琉璃一般脆弱的美人,白鹤一般兀傲的文士,他们的遭忌更是不言可喻了。试想含意未伸的文人,他们在不得意时,有的采樵,有的放牛,不仅无异于庸人,并且备受家人或主子的轻蔑与凌辱。然而他们天生得性格倔强,世俗越对他白眼,他却越有精神。他们有的把柴挑在背后,拿书在手里读;有的骑在牛背上,将书挂在牛角上读;有的在蚊声如雷的夏夜,囊了萤照着书读;有的在寒风冻指的冬夜,拿了书映着雪读。然而时光是不等人的,等到他们学问已成的时候,时光是早已花了,头发是早已白了,只是在他们的头额上新添加了一些深而长的皱纹。
咳!不如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读“人生”
这本书罢!
书本世界
金克木
话言化为文字,换了符号,成为文本或一本书,又出现了另一个语言符号世界。书本世界不能完全符合口语世界。书本被创造出来以后自成一个世界,自有发展并且限制了进入其中的人。人进入书本世界以后常常通过书本认识世界,和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可大可小的,它不是一个人单独创造的,也不是人人相同的。
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讯(交流信息)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样。不同的语言说着不同的世界,或则说是宇宙的不同世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都能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见到一排符号,站在无形的封闭的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
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认识的人只知道外形,对认识的人就知道他的或多或少的事,也就是这个人的世界。严格说这只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组合起来的那一部分,不是那个全人。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造成一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来源,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这些都可以用读书来比譬。从一个个字和一个个句子结合读出整个文本的内容,也就是由解说构拟出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语言(口语、书面语、数学语言、艺术语言等),有各种语言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世界中,有的人的世界层次少,有的人多。
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这真是如《楚辞》的《九章·涉江》开头所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可惜我把语言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世界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注释的书,而且对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知心的书
鹤西
年岁大了,老友逐渐减少,交往中却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亲切而坦率,可惜都相隔遥远。去年自己被撞骨折,虽然恢复得还好,也少有外出了。翻到《水浒传序》说的“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不免古今同慨了。然而人总得有一点精神上的交往,没有朋友面谈,书或者也可取代吧。
过去我写过几篇散文,谈自己和书的因缘。是的,年轻时我买过一些好书,回忆这些书,我曾经写道:“书是无声的和我们共患难的朋友,我和我的书的聚散,又是一本无字的书,它记载着人世的沧桑,现代的历史。”其实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和我患难与共,朝夕相处的书,屈指数来也不过三五本而已,其中两本还是工具书,说得上知心之友的实际只有1914年出版的AlexanderSmith的《梦村》(Dreamthorp)注释本。虽然也是牛津出的,却不是世界名著丛书中选文更多的版本,定价为一先令,只看这个价目,我也就恍如隔世了。
斯密斯先生大约算不得名家,我们可以说是布衣之交;而更重要的是在我读过的西方文人中,很少看到哪一位有他这样浓厚的东方气息。让我们看看他对“梦村”第一印象的描述吧:“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将近八点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梦村,它的西向的窗户染着夕阳,小孩子们在一条错落的街道上玩耍,妈妈们坐在门口做针线,爸爸们穿着白色的长衫,有的在闲谈,有的在抽烟;那废垒的塔楼高耸在玫瑰色的空中,一大群燕子---远看像蚊子似的---在它的缝隙四周飞翔;当我一眼看到这些,我就本能地觉得我可以歇下肩上的行囊,我的疲惫的双足也可以不再流浪,在这个地球上,我终于找到一个家了。”
在《书和小园》里他写道:“我还是就这样生活更为快乐。我没有必要去制造历史,已经有大批的人愿为我代劳了。”“在小园里我消磨我的白天,在书房里我消磨我的夜晚。我的兴趣在天竺葵和书本之间。在花丛中我享有现在,在书本中我享有过去……我像坐在戏院里一样,时间是舞台,上演的就是世界这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