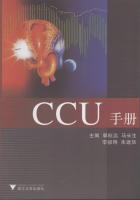明白了这道理,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何长期对国民党持一种既拥护又批判的态度了。数十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与对抗来说明。即便在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得最紧密的时期,这种对抗也仍然存在。出现很严重的对抗并招致国民党的打压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权运动”时期,一次是在晚年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时期。这里只简略说说“人权运动”时期的情形。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蒋介石便开始极力推行“一党专政”,并积极谋求个人独裁,明显地表现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倾向。面对此种局势,以胡适为领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蒋介石本人,也发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责。在“人权运动”期间,胡适一人就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作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中,胡适指出“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在胡适举出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两文,则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国父”孙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后者批判的是孙中山“行易知难”的“哲学思想”。在前者中,胡适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因为“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在这里,胡适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当“民主政治”方面的小学生。《知难,行亦不易》,更是对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系统批驳。《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则是胡适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反动思想”的严厉清算。胡适认为,国民党执政后,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而是一种“反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了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歌颂传统文化、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之类的话,然后指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接着,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文化问题”三个方面,论证了国民党的“反动”,并且说:“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胡适在为国民党确立了几条改革目标后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不久,“人权运动”中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胡适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对国民党的反抗,不仅表现为言论,也体现在行动上。其时,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内,不挂国民党党旗,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这更是对国民党极力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抗拒。
面对胡适等人的“挑战”,国民党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南京等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后由教育部发出“训令”,对胡适予以警告。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这些批胡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认为胡适的言行已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反党罪”。在批胡运动中,国民党要人潘公展亲自督战,后又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潘公展为此书题签书名,并且预告还要出版第二辑。批判胡适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知道,大陆50年代的批胡文章,曾汇编成八大辑,由三联书店以《胡适思想批判》为名陆续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批判文集。与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几乎同时,台湾也开展了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蒋经国所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对胡适发动了总攻击。倘有人将1929年出版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发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进行比较,一定饶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由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编辑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结集出版,现代中国文化人中获此“殊荣”者,除了这“二胡”,我想不起还有谁。而从国共两方面都受到以此种方式表示“重视”者,似乎只有一个胡适,仅此一点,也可见出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分量”。
胡适对国民党的种种批评、抨击,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从封建帮会式的政党改造成现代英美式的民主政党,这是要让国民党脱胎换骨、改魂易心,是要从根基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是反国民党的,也并没有错。而另一个“胡”——胡风的“反党”罪名,可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感情和态度,与胡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感情和态度,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胡适是俯瞰,是教训,是“恨铁不成钢”的希望和失望。而胡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仰视,是膜拜,是近乎无条件的信奉,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随。他仅仅是在一些具体的文艺问题上与主流观念有所龃龉,而且,他始终坚信,这种龃龉只是发生在他与其时掌管文权的周扬等人之间,是周扬等人误解和歪曲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文艺思想”。
除了声望、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外,胡适与胡风之间还有着太多的不同。在1949以前的文化界,胡适是自由主义群体的主帅,胡风则是左翼阵营的中坚。可以说,那时二人是相互敌对的。对胡适所倡导的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实从未真正弄明白过。而在被认为“左得出奇”的胡风眼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忙”或“帮闲”。有趣的是,在自己被视为与胡适同类的不久之前,胡风还在起劲地批判胡适。1954年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批判《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压制小人物”的错误,胡风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胡风首先批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具体的讲‘是向反动的胡适派思想投降’,胡风点出朱光潜的例子,认为朱光潜过去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对这样的人,《文艺报》却妥协、投降。”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宣告成立,胡风就以无比的真诚写了长达数千行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尽管遭到打压,胡适至死不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判态度。1980年3月,从四川回到北京后,胡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道:“我一直认为事情总要有个相当的结束,所以对释放并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会乱打一个人,乱杀一个人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听天由命,天是中央,是党,命是事实。”①1980年11月15日,胡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一文,这是二十六年后首次亮相,胡风写道:“我想到了党,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三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我、教导过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的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其实,他至死也没有看到对他的“彻底平反”。
①见李辉《文坛悲歌》。
胡适与胡风的最根本区别,还在于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传统型的文人。胡适虽也多多少少有着传统士子的气息,但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胡风虽也多多少少具有现代意识,但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型的文人,他的气节,他的情操,都是传统型的。胡风挚友贾植芳先生曾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书,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不能容人。”①
①见戴光中《胡风传》。
尽管胡适与胡风有着种种不同,但在大陆50年代的“批胡”运动中,他们还是被一锅煮了。假反共产党的胡风被说成是真反,真反国民党的胡适被说成是假反,这也应了一句老话:“假作真时真亦假。”
2001年2月5日
①见李辉《文坛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