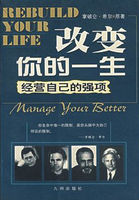我沿着那泥泞的道路走了很久很久,终于踏上了一条狗头石铺成了石头路,并没在石头路上走多远,就遇上了一对好心的小贩。男的胡子拉渣的驾着一辆破旧的带蓬杆的三轮车,女的搭着一面花头巾,坐在车里的甘蔗上面。
他们把车子停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女的使劲地向我招手。我不舍地捂着兜里的碎钱,小心地移步向前。结果,他们非但没要我的半分钱,还折了半截甘蔗送我吃。于是,我搭着他们的车子进入了县城。
到了县城,临下车时,驾车的男人才扭头对我咧咧一笑说安九,我知道哩!你这个小杂毛!你爹和我小时候和过尿泥呢!我一听吓得跳下车拨腿就跑!担心他把我再带回去交给毕明他堂叔。我一直跑啊跑啊,直到腿脚发麻,实在跑不动了才停下来。举目四望,车水马龙,却没有半点熟悉的模样,这才放下心来。然而,肚皮却饿得叽哩咕噜一阵乱叫。
我挤进一家小面馆里要了一碗面条,汤汤水水全部下肚后,好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容身之处。我索性壮起胆子问面馆老板要不要人,想留下给他当小工。老板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我识趣地走了出来。漫无目的地瞎逛。
一路上我遇到几个像我一样的小孩子,穿得破旧不堪,手里举着一个碗向路人讨钱,竟然真有不少人往那碗里丢钱。我高兴得直拍脑袋,有了!老子也弄只碗来要钱去!说干就干,我原路返回了面馆,挤进去摸了一只碗藏怀里。不料,刚出面馆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衣领!
“狗娘养的!老娘就说这几天这碗杂越来越少!”
一肥婆子话音才落就给了我两记响亮的耳光。直打得我火冒金星,辩不清东西南北。接着又朝我屁鼓狠狠上了一飞腿。她这一飞腿直接为此后我不喜欢女人埋下了祸根。
“行了,你真想打死呀!”
就在肥婆子准备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时,一直忙于给客人下面的老板终于开腔了。
“打死活该,这有人生没人养的狗杂种!”肥婆子似乎真的还不解恨。
我哪里还顾得什么疼痛,起身就拼命地跑。最后竟然撞到一位壮汉怀里。
“嗯哼!”壮汉言简意深,一双眼睛凶残地瞪着我,像一只恶狼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公鸡。
“对不起,对不起!”我心都快给吓出来了,慌忙跪下给他赔不是。
壮汉慢条斯理地说:“对不起也没有用!你看看你把我专治爱滋病的特效针水都给整废球了!我这人特别讲道理,这针水呢在医院在八百块钱一支,十二支一盒,你自己说这两盒针水你得赔我多少钱?可关键是你赔我多钱都没有用了,这针水弄不到了!会死人的!”
我一愣,脑子一热,什么八百一千的,我最大也就见过面值十块的毛爷爷。再低头一瞧,地上果然有两盒打翻的针水盒。跟着便哭着蹲下身去捡。
“哭也没有用!赶快带我去找你父母来处理吧!”壮汉说时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抓了起来。
我看到他胸口那道道刀疤,哭得更厉害了。
我老是哭,壮汉拿我也没法。换一位相对温柔的大姐姐来对我循循善诱,想哄骗我带她去找父母要钱。当得知我是一孤儿后,她一改温柔的样子,一番吹胡子瞪眼后,朝我屁鼓恶补了几脚。然后,悻悻地离开了。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只是派人远远是跟踪着我,想看我去哪里。她们始终都不相信我会是一个孤儿。这其实要归咎于那位好心大娘把他小儿子的衣服给我穿上了。
时间过得太快,天很快就黑了下来。我无家可归,晃荡到了天桥底下。不想早被两位老伯伯占了先机,把我给赶了出来。
“去去去,快回家找你爹妈吧!不要让他们东找西找的,担心!”
原来,他们也以为我是有家的人,以为我与爹妈闹别扭赌气离家的呢。
我尝试向他们解释自己当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毫无用处。最后,其中一位老伯解开了拴着的一条小黑狗,汪汪汪地直叫着想来追咬我。我不得不逃离了心生留恋的天桥。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一直跟踪我的人终于站了出来,重重地拍了拍我肩膀,朝我伸出一中指,神气十足地叫道:“小样,跟爷走吧!”嘴上说着是爷,其实年纪与我相仿。其实我早就知道他那女坏蛋派来监视我的,但我聪明了一次,没有说破。
他把我带到城边上的一座烂尾楼里,白天抓过我的那位壮汉也在场,他正和五个男人围着空地上的一堆火,火上高高地架着一烧烤架,架子上放着些肉烤着,他们说着荤话喝着啤酒吃着肉。那壮汉似乎还记得我,看见我把手里啤酒瓶直直地扔了过来,差一点就给他砸中了。
带我来的那小子回了一句:“肥哥!想死噶!”接着我们上了二楼,拐弯处又碰上了白天吓唬过我的那位坏姐姐,她已经换上了艳丽的超短裙,提个挎包装备和另一位同样打扮妖艳的女孩子出去。上了楼,没有装饰过的房间里有七八个年龄不等小孩子,他们正在一位年纪稍大的大姐姐的带领下精心地数着碎钱。在他们旁边摆放着些肮脏的衣服和破碗。我顿时明白了,他们就是白天我所见到的乞儿。
难道我真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穿一身烂衣抬一个破碗向一只狗一样向所过路的每一个摇尾乞怜?
我不知道,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第二天,他们只让我认识了“团队”里的十七个人。然后,让我和另外一位小女留在“家”里做饭。
后来,我才弄明白,“团队”分工明确,肥哥一伙五人负责诈骗;咧咧姐一伙三人在KTV陪侍;明仔一伙五个小孩负责乞讨;滔仔一伙四人负责偷东西。不过,滔仔一伙中的晃仔刚刚被调去别的地方发展下线。正因为这样,我被安排在滔仔一伙,跟他们学偷东西。
一个月后,我成了一名手法老练的偷儿,像滔仔他们一样,兜里随时揣着几张锋利的刀片,轻易就能把别人贴身的钱包、裤兜给划破,把钱取走。他们也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九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