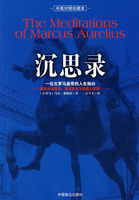青牛像是听瞳了他的话,不断用头蹭着李耳,表示是自己做错了。
青牛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要这样走回函谷关是不可能的。尹喜和徐甲又从远处借来一辆车,把青牛放到上边,用车拉着它回函谷关。
车就要出发了,尹喜却把车停住说:“先别急着走,让我抱几块黑东西放上。”他就去抱了几块黑东西放到车上,高兴得把一块黑东西在自己的衣服上擦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煤。嗨!青牛又立了一大功,在这里发现了煤窑,以后函谷关老百姓的烧火做饭问题就解决了。”
此后,尹喜领着些人在这里开煤矿。周围几十里的人们都来这里拉煤,不管是马车拉,还是骡子驮,排的队伍再挤,只要是牛车来了,就会自动让开一条道,让牛车先拉。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一直沿袭至今,可见人们对青牛发现这个煤矿的尊敬。
李耳、尹喜、徐甲赶车拉着青牛,经过两天多的行程,这天下午来到函谷关南边的郊外。猛然看见有一群狗在咬着、拉着,不一会儿把几个用乱草裹着的东西拖到了路上。草裹被狗嘶咬开了,竟是几个小孩的尸体,被狗咬的血淋淋的,真是残不忍睹。这是怎么回事?
函谷关副关令孙景这时跑来,向尹喜报告说:“这些天,函谷关流行一种可怕的瘟疫,人一但患上,浑身发高烧,打颤不已,接着就是狂奔,继而眼睛失明。特别是小孩患的更多。这不,你们瞧见了吧,”他指着路旁狗咬的“死娃”又说,“这里有一个习惯,小孩夭折后不埋葬,用谷草或麦杆裹着尸体,送至村外放于‘天道处’(路旁),让狗啃食。据说这样处理,来世仍可变人,否则,永为孽鬼。”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抑制这种瘟疫的蔓延?”尹喜问孙景。
孙景答道:“我让胡涂梦大夫想法找出一种新药,来医治这种瘟疫传染。据胡涂梦医生说,新药研制得差不多了,现在就缺一种药。”
“缺什么药?”
“这我不清楚。”
“那我俩先去看看胡涂梦医生,看到底缺什么药?”尹喜和孙景快步走了。
孙景说起胡涂梦医生,使李耳想起他的孙女胡逗逗来,那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儿歌唱的可好了。那次他著书累了的时候,就是她来给自己唱几首歌解闷的。不知道她是否患上了这种瘟疫?李耳是怀着这种心情进入函谷关镇的。进到函谷关镇,果然看到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一盆水,盆上架着一把刀,凡是进门的人都要撩水于刀上。
李耳不明白这是干什么,一问才知道是自从这种瘟疫蔓延后,说是用这种方法能防止带入邪气。人们在不明白这种瘟役的病因前,只能用这种方法祈祷平安。
李耳和徐甲把青牛安顿好后,便直奔胡涂梦医生家。这是李耳早想拜访的,只因著书太忙,一直没时间来。
胡涂梦的家住在一个小院。李耳推门进来,只见一道寒光闪过,胡涂梦手里的长刀哗地一拉,一头黑牛收敛起哀怨绝望的目光,全身闪电般颤抖起来。紧绷的脖颈先是出现一条白亮的口子,然后乌黑的血沫向四周喷射,呼呼的喘息声把黑牛的生命一丝一丝地抽出后,又弥漫成浓烈的血腥味。
“嘿,真是头怪牛,临死了都不挣扎一下,真没出息!”胡涂梦在黑牛毛茸茸的背上熟练地抹着刀上的血迹。他一抬头见是李耳和徐甲来了,忙说:“你看我这个刽子手满手血迹,怎好招待你俩,不嫌弃的话,就先坐到凳子上。”说着,他用脚踢来两个小凳子,让他俩坐。
李耳没有坐,而是站着问:“这头牛好好的,为何要杀它?”
胡涂梦见刀子上的血迹没有擦净,又在自己的裤腿上蹭了几下,说:“刚才尹喜、孙景来了,询问研制治瘟疫的药缺什么,其实就是缺牛黄。现在到哪里去找牛黄,我估摸着自家的这头牛身上有牛黄,就把它宰了,看它身上到底有没有牛黄?现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看运气……”
他的话还没说完,只听“哞——”的一声长吼,黑牛猛地挣扎着要站起来。
“有种的,点髓!”胡涂梦握着明晃晃的刀朝黑牛脖子上血口游了进去,恰到好处地点了一下,一股乌黑的血迹随着刀流淌出来,黑牛不动了,死不暝目地瞪着握刀的胡涂梦。
胡涂梦哆哆嗦嗦地低下头,再也不敢看黑牛了,“快把黑牛的眼睛用布遮上,我真害怕再看见它那双瞪着我的眼睛。”
胡逗逗拖着病弱的身体,从里屋拿出自己穿的一件小花衣,遮在牛眼上,“爷爷,您的心也太狠了,怎能杀了咱家这头唯一的黑牛,我看以后犁地没有牛了,您自己拉!”
“爷爷也是没办法呀,为了救更多的人,也包括你,只有杀这头黑牛了。”胡涂梦狠狠地用左手掐着自己的右手腕子,他是不得已才下这个决心的。
“那是李耳爷爷吧!”胡逗逗被瘟疫折磨得只剩一把小骨头了,原来胖乎乎的模样全不见了,眼睛也看不清楚。
李耳赶紧把胡逗逗抱在怀中,“是李耳爷爷来看你了,快给爷爷唱首儿歌,”他想用歌声把胡逗逗从病痛中唤过来。
“李耳爷爷,你再用白胡子扎扎我的脸蛋。我真想你呀,你怎么不到我家来。”
李耳用他的白胡子轻轻吻着胡逗逗的脸蛋,“痛吗?”
“一点都不痛,你的白胡子就是没有我爷爷的黑胡子硬,他每次都扎得我叫了起来。李耳爷爷,你看我的病能治好吗?”
“能治好的,一定能治好的。”
“那等我好了后,再给你唱儿歌。”
“别在那里闹李耳爷爷了。”胡涂梦对着孙女胡逗逗说,“快下来,到屋里去,爷爷现在要剥牛了,你是不能看的。”
胡逗逗很听话地从李耳身上下来,回到里屋去了。
胡涂梦又从屋里取出一把牛耳刀,开始剥牛。牛耳刀宛如一只飞舞的银蝶在黑牛身上游来游去,随着阵阵悦耳的沙沙声,黑牛乌黑油亮的毛皮渐渐退去,露出白白的肉。他边剥边对李耳说,“杀牛最讲究点髓,牛临死的时候都会憋住最后一口气,留住最后一碗血。点过髓的牛,肉鲜、易煮、不腥、少血污,当然也是最好吃的。”
胡涂梦慢慢进入了剥牛境界,满脸惬意。刀沿着牛的骨骼间走,剖开牛骨骼间的缝隙,顺着筋骨间窍穴进刀,按照牛本来的生理结构解牛。不一会儿就把牛解剖完了。
现在就看黑牛有没有牛黄了,在场的几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心提的最高的当然是胡涂梦了。他把牛胆摘了出来,放到一个脸盆内,然后用刀子划破,等着那块牛黄出现,令他失望。他用手在胆里摸着,摸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气得他又把牛胆掂到眼前翻看着,哪怕找到像玉米粒那样大的也行,可是什么都没有。
本来是站着的胡涂梦,看到没有牛黄,一下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这牛是自杀了,怎么运气这么不好,连一粒牛黄也没有。没有这味药,怎么能抑制住流行的瘟疫?”说着,他抱头大哭起来,哭得是那样伤心,那样悲痛,简直像杀了他似的。
李耳连忙拉住他,劝道:“不要再这样哭了,哭多了是会伤身体的。你说说,牛身上有牛黄,会有怎样的表现?”
胡涂梦抹了抹满脸的泪水,“简单地说,牛身上有了牛黄后,长吼,眼如血色,害怕人,又喜欢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