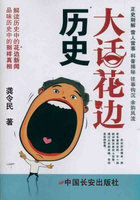那个时候,武威还未由县改市。张义堡乡还叫张义人民公社。由县城到公社大约七十五公里路程,还不通公路班车。我们不愿麻烦县里派车,就只有到公路上拦车了。甘新公路上车来车往,通往张义公社的车不多。终于拦截了一辆路经张义堡的解放大卡。那时候还不是商品社会,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只要司机高兴,乘车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出示工作介绍信就可以搭车。卡车上空荡荡的,只在车厢一角放着一个备用的汽车轮胎,它便是我同史金波的座位。车行在平坦的甘新公路上倒也舒适。
拦截过路车或搭便车是当年长途跋涉从事民族考察工作者都经历过的。记得1960年我在西藏搞社会历史调查,一出门几百上千公里,没有专车,就只有拦车和骑马两途。乘一小时汽车就等于骑一天马,所以我们常常蹲在路边或道班、兵站等车。有一次,我们几人在藏北高原公路上搭上一辆烧柴油的大型军用卡车,汽车冒着黄烟,在冰雪高原上日夜行走,我们自带行李躺在卡车上,像在大海上行船。夜里星光灿烂,似觉伸手摸到星辰。那年夏天,我和藏族翻译普穷从错那宗勒布地区的中印边境上返山南泽当,是搭乘一辆装炸药箱的军车,这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如果骑马,就必须经历七八天日夜兼程的旅途辛劳。改革开放以来,出门极其方便。我说有“三方便”:即住宿、吃饭、坐车。出门乘车之便令人难以相信,但要有钱。于是就演出一幕幕悲喜剧来。如果一一记出就得再写“七记”——“乘车记”了。这里打住。
还是回到1976年9月初的甘新公路上。我们到武威的考察重点之一就是张义公社的下西沟岘山洞。两年前,还是百家齐喑,似乎独宗“考古”时,我在《考古》杂志上看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的《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的报道,介绍了1972年1月间,武威张义公社下西沟岘社员群众在山洞上挖药材时,发现西夏时期遗物的情况。到下西沟岘考察早就列入我们的考察计划。
汽车向东南行,到黄羊镇后转向西南,进入土路。车体剧烈地颠簸着,我们也跟着车胎上下跳动,消受不了,只好站起来扶住车厢板,任河西走廊上初秋的凉风吹拂。好在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公社所在地张义堡。公社派一五十多岁的农民作向导领我们去下西沟岘山洞。
张义堡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盆地。据考张义乃张掖谐音改,其地西汉为武威辖张掖县驻地。明代筑堡,村落以古堡为中心,南北扩展。因地处黄羊河上游山间盆地中部,南通祁连,北通凉州(武威),自古为交通战略要地。公路南通天祝藏族自治县之哈溪滩。下西沟岘山洞距公社所在地五华里左右,出张义堡便进入山间羊肠小道。西北行,抬头见群山耸峙,山坡下偶见补丁似的梯田,星星点点。进入山中,眼前一条曲曲折折的山沟由北向南倾斜而下,两旁的山峰像用巨斧劈开一样平行对峙。在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三个卷槽”的山坡,面向西南,上面是一处塌陷的山隙,这是到此的羊倌牧童躲避风雪栖身之地。
向导领我们爬上山坡,仰望山隙中部有一个不足一人高的山洞,洞口杂草丛生,乱石嶙峋。我和史金波跟着向导攀岩而上,进入山洞。洞窄而深,极不规整,黑黝黝的。借助手电的光亮,看洞中已无一物。据说这里曾发现过少量的西夏遗物。洞的上部还有一个可容人的小洞,洞口原装有门封闭,当地农民挖药材时打开进入。洞已被毁,形制不清。洞中还有佛座、倒毁的泥塑佛像、壁画和大量的善业泥。佛座上涂抹一层白灰泥,上面写有红色的西夏文字。壁画上似有题记,已看不清。洞中还有小土塔一座。在此洞北约二十米处,还有一个石洞,当地农民叫它“修行洞”或称“鸽子堂”,洞中没有发现过西夏遗物。据说清末民初时还有和尚、道士在这个洞中修行,洞顶还留有烟熏的痕迹。
下西沟岘封闭过的那个二层小洞(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2号洞)中曾发现珍贵的西夏文物近百件,种类颇多,内容丰富。有西夏文刊本《杂字》残页、佛经写本和刊本残页、西夏文写本医方。会款凭证、占卜辞。西夏文木简。汉文文书有官方文书、布告、请假条、欠款凭据、便条、日历。藏文刊本和写本佛经。竹笔、木刮布刀、生牛皮鞋、皮条、毡片、石纺轮、石球。宋朝和西夏钱币。苦修像和善业泥。2号洞出土的两身苦修像,一身是泥塑像,锥体形,高7厘米,底宽5厘米,厚1厘米。塑像头戴山字形冠,盘膝而坐,右手置于胸前,左手下垂,背火焰,骨瘦如柴。另一身为铜铸,高7.5厘米,宽4.8厘米。亦盘膝而坐,双手交置腿上,胸部显露肋骨嶙峋。根据洞中出土遗物如苦修像、制作简单的生牛皮鞋、捻线用的石纺轮、织布用的木刮布刀、瓷碗、芨芨草编的席子、铁刀等,多次到此调查、清理洞窟的西夏学家陈炳应先生判定2号洞是一处经人工修建的“修行洞”遗址。据洞中出土文献的西夏纪年:最早为夏人庆二年(1145),最晚为光定二年(1212),说明洞中所藏是西夏中后期的遗物,推断这个“修行洞”的废闭大约是在蒙古灭西夏的时候。张义堡地当河西走廊交通要道,为蒙古灭西夏必经之地,此洞可能在战乱中被封闭,所以在洞中没有发现元代的遗物。
下西沟岘“修行洞”近八百年的封闭,收藏了一批西夏时期的遗物,1972年被发现时却给它带来了灾难。据说,起先是当地群众上山挖药材时在山洞中发现了大量的“五灵脂”中药材,这是生活在茂密树林中的鼯鼠或类似的多种动物的粪便。当社员群众们进洞去挖掘“五灵脂”时,在下面发现了叠压着层层的古书残纸,拿来一看,仿佛是汉字,却又谁也不能认识一字。个别天真而又愚昧的社员群众认为这是扰动了“天书”。祸福不知,赶快焚烧,使其“归天”。究竟烧毁了多少是谁也说不清的。当地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员制止,上报文物部门进行调查、收集。1974年3月公布发现的那些西夏文献、遗物已经是劫后的余存。
下午返回武威县城时,我们搭乘的是一辆运煤炭的卡车。途经著名的天梯山石窟我们却无缘拜识。卡车上,午后河西的风沙肆虐着,我和史金波与煤粉共舞。我看着他,想起了我山西家乡下煤窑的“窑黑子”,心中好笑。当我发现他也望着我笑时,才意识到此时此地彼此彼此。这副嘴脸如何能进得县城!所以车快到县城时,我们请司机在城郊的公路上停车,在路边找到有水的地方洗净了手脸,步行回城。
20年过去了,1996年8月底至9月初,我和史金波赴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结束后又沿河西走廊作旧地重游。又是金秋艳阳天,来到改为县级市的武威市,这里已被国家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些年见诸报道,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武威在市区建设中,以及在市郊的新华乡山村、古城乡塔儿湾村等地维修寺庙,兴建学校、文化室及农田基本建设中又出土了大量西夏时期的文物、文献,如铜器、铁器、陶瓷器、石器。玉器、木器、丝织品、泥塑、帛画、西夏文书、佛经等近九百件。1995年夏,在宁夏银川召开西夏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曾亲自参与对这批文物文献发掘整理研究的武威市博物馆负责人孙寿岭、党寿山二位邀请我同史金波赴武威参观。
武威新发现的西夏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塔儿湾的瓷器和亥母洞的西夏文字文献了。9月6日下午,现任市文化馆书记的孙寿岭和市文管会黎大祥同志亲自陪同我和史金波去遗址考察。计划是先去位于市郊东南沿山一带的新华乡山亥母洞寺遗址,然后奔古城乡塔儿湾村瓷窑遗址。车还未离开市区,红日高照的晴朗天空,渐渐阴沉下来。当汽车进入渠边小路逼近山下丘陵地区时,已是彤云密布,山雨欲来。古城乡的塔儿湾村在祁连山余脉的冷龙岭下,无公路可通,只有一条近十华里沿山小道,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司机说我们乘坐的北京吉普勉强可以进山。为抢在大雨之前进山,我们便改变原计划,先直奔塔儿湾村。心里捏着一把汗终于进了塔儿湾村。才进入村口,放眼望去,四山环绕,一水中流;山下阡陌相连,山坡梯田层叠。河岸高处绿树掩映下,一座座黄泥小屋,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田野间,场院上正在干活的农民频频注目我们这不速之客。车刚停在村口路边,村民与一位村干部迎了上来,我才知道这里原来就是孙寿岭同志的家乡。他曾经在这一带担任过多年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师,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村干部和孙寿岭带我们爬上山坡去看窑址遗迹。这里的瓷窑遗址是村民们挖土建房时发现的,土崖下灶台建筑、朽木灰层犹清晰可辨,到处是残碎瓷片,随手便可拣到。我们进村时一群刚放学的二年级小学生,像小麻雀似的蜂拥跟着我们上崖跳垅,拣了大堆的瓷片向我们“献宝”。据说古城乡烧制瓷器历史悠久,附近有一座名为窑城的古城遗址,相传瓷窑最多时可达48座。附近曾发现过唐高宗永隆年间(680—681)的铭文瓷砖。1992年在塔儿湾村遗址出土的各类瓷器,经市博物馆修复成形的有140多件。我们在市博物馆的仓库中参观了这批瓷器,其中有一件西夏剔花牡丹瓷罐高65厘米,腹径49厘米,是我看到过的西夏瓷器中最大的一件。有一件已残的瓷瓮底外沿墨书汉文“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此为西夏神宗李遵顼光定四年(1214)之物。
正兴冲冲参观遗址,拣拾瓷片,蒙蒙细雨下起来了。我们急速开车下山。司机说这里山路一经雨后油滑难行,有时几天出不了山。直到车开出山口我才放宽了心,冒雨钻出车来拍照,回眸远山黛色,近水泄银,烟雨苍茫,疑是南国风光。
下山后,车往北返,顺着渠边便路去找亥母洞。
来到武威,原野上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是纵横如网的渠道,历史上被誉为“银武威”,是河西走廊戈壁大漠中的晶莹滴翠的绿洲,全靠来源于祁连山雪水的灌溉。数不清的网状的渠道便成为武威生命的血脉。我们所经过的渠道,都能看到约十几米宽的石砌堰道中,略呈银白色的雪水奔腾一泻而过。渠道两侧是笔直耸峙的杨树林荫小路。
5时左右,车到山脚下,依然是细雨霏霏。我们不进村,先径直冒雨上山,请文管会黎大祥同志进村去找管理山洞寺庙的人。这里是山北麓,绿色植被下裸露出呈土红沙岩的石山,几处如屏障般的巨石交错着,石缝隐隐地往下伸延着,我想那里就是山洞了吧。我们一行人越过一条干涸的河道,沿羊肠小道蜿蜒而上。半山腰上有一座砖筑小庙,神台上摆设着不知从哪里取来的几尊极小的泥塑,似佛似道,其他空无一物。继续爬上山腰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开阔地,深入山腰二十多米处,一列自然形成的高大山洞,巨石如刀削斧劈般相互支撑架空。洞口坐西向东,深入山体与主体洞相连。主体山洞是自然形成的,南北走向,深不可测。相传此洞和大山背后青海省西宁的塔尔寺相通。
深入山腰一字排列有四个大型洞窟:进山路口上的第一个洞窟,附着于洞口的有新建的庙门,是用水泥和砖石整修过的。门楼上镶嵌的是原有的砖刻“大雄宝殿”四字。庙前废址上残留着铺地的方砖,据说是明清时期殿堂的旧址,大约有十五平方米左右。山村管理洞寺的两位老年人慢慢走上山来,一见我们面,便双手合十,作佛家礼。我称呼他们大娘、大爷。他们拿钥匙开了山门,洞中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大娘点上了蜡烛,引我们摸入后洞,洞有四五平方米左右,有舍利塔四座,泥塔婆堆积满地,拿一个打开,里面有大米粒大小之“舍利子”与一张印了藏文字的小纸条。后洞门洞上新镌“孩母洞”水泥匾。前洞香案上供品法器杂陈,暗中无法细看。一旁竖一碑石拦腰残断,碑额似有线雕,借助灯火仅辨清碑石上有“亥母”二字,而不知其年代。出第一洞,旁边的三个洞,洞口巨石凌空欲坠,有的已堵住洞口,我们不敢冒险进入,只在洞口拍照。据孙寿岭同志介绍,山位于河西走廊的地震带上,曾经过多次地震的破坏,呈粉碎性塌陷,洞窟都被塌落的岩石填塞。在第一个洞窟殿堂南墙中断的岩石中,曾经发现一身着羊皮袄、肩背褡裢的男性直立骨架被挤在岩缝中,死者可能是死于地震的朝山香客。
山北麓是武威早期石窟寺址之一。据《武威县志》载:“孩(亥)母洞,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修。”正德乃西夏崇宗正德四年(1130)。据说此处洞窟四周三华里的范围内都有西夏时期建造的寺庙、佛塔遗址和遗物。亥母洞遗址中出土了丰富的西夏遗物,如佛经类有木刻本和写本的西夏文多种佛经,泥活字印本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唐卡、佛画、藏文佛经。文书类有西夏文《音同》残页,西夏文处罚、典卖契约文书。器物类有褐釉瓷扁壶、花色丝织品、妇女和儿童绣花鞋,以及泥塑、石佛造像、浮雕、哈达。西夏文和藏文佛经散见于各洞中;一些契约文书、西夏文经卷和褐釉小扁壶则发现于殿堂南侧被挤死的香客身下的岩缝中,可能是西夏香客的遗物。
世间之事,无独有偶。亥母洞西夏文文献的发现与张义堡下西沟岘“修行洞”西夏文献的发现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时当1987年5月间,山村民们自发捐款修复亥母洞寺庙的“大殿”。施工中于地砖下发现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西夏文字经书。当时乡里正在开展“扫黄”和“除六害”运动,乡政府发现村民有人又在修建寺庙,搞封建迷信活动,多次派干部到村里追查修庙的带头人。村民们害怕了,又见洞中挖出的经卷文书内一个字也不认识,遂认作是“天书”,怕招来祸祟,竟当作黄色迷信品付之一炬。剩余的一少部分,被几位虔诚的佛家信徒老人偷偷藏于洞内石缝中,得免遭焚毁,幸存下来。
1989年9月中旬,武威市公安局治保股股长徐建祖同志下乡工作,来到山村亥母洞察看,发现了被遗散在山洞中的西夏文佛经残页。有心的徐建祖同志顺便带回了一页,交市博物馆的负责同志辨识,同时介绍了亥母洞的情况,这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才有了出头之日。当时担任市博物馆书记的孙寿岭与市文管会副主任党寿山副研究员遂赶赴山村,考察了亥母洞现场,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法令,动员大家把拿走的文物经卷交回。最初被村民们修庙时发现的西夏文经卷有多少?被当作黄色迷信品烧掉的有多少?散落民间至今未能收回的有多少?多年前我在北京,这次我在兰州都听说过一个“两麻袋”之多的数据,它究竟是指哪一种,都无从考察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