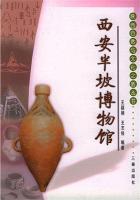“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两天前首次见到你时的情况,当时我知道的也并不比你多。你会问詹姆士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只能说,詹姆士心中有一种无法解释和难以想像的对我合法继承人的憎恨。他恨自己不能得到我的全部财产,恨那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法律。他希望我能不顾法律的约束,在遗嘱上写明把财产留给他。他想方设法不使阿瑟成为继承人。他清楚地知道,我绝不会把他出卖给警察。我肯定他准会那样要挟我,但事实上不是那样,因为事情发展之快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你发现了黑底格的尸体,这使他大为惊恐,也打破了他的邪恶计划。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二人正坐在书房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拍来一封电报,詹姆士忐忑不安,所以我由怀疑马上变为肯定。他彻底地承认了一切,然后他哀求我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三天,以便给他罪恶的同谋保住性命的机会。对他的哀求我让步了,我对他总是妥协的,他马上赶到旅店警告黑斯,并且资助他逃跑。我白天去那儿一定会引起议论的,所以夜晚一到,我便匆忙地去看我亲爱的阿瑟。好在他安然无恙,但显然暴力事件使他受惊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我答应把孩子再留在那儿三天,由黑斯太太照顾。显而易见,向警察报告孩子在那而不说出谁是元凶是不大可能的,而且相当清楚的是,元凶受到惩罚不会不牵扯到我可怜的詹姆士。福尔摩斯先生,你希望我坦诚相告,我相信你的话,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一切。你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坦率呢?”
福尔摩斯说:“会的,公爵,我首先告知您,在法律上您处于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您宽恕了罪犯,并且协助杀人犯逃脱——因为我不能不怀疑,王尔德给他同伙用于逃跑的钱是从您那儿得到的。”公爵点头表示承认。
“这件事的确很严重,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您居然同意把您的儿子继续留在虎穴里,而且是长达三天的时间。”
“他们严肃地做了保证……”“你居然相信他们那种人的诺言和保证!您能保证他不会再被拐走?为了给长子隐瞒犯罪事实而使您无辜的幼子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不公平的。”傲慢的霍尔得瑞斯根本不习惯在自己的家里受到如此批评,他的脸从前额红到下巴,可是理亏使他沉默。
“我会帮助您的,可是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您把您的佣人叫来,我要按照我的意愿发出命令。”公爵一言不发,按了一下电铃。一个仆人进来了。
福尔摩斯说:“你一定很高兴你的小主人找到了。公爵希望你立刻驾驶马车到‘斗鸡’旅店把萨尔特尔勋爵接回家来。”
仆人高兴地走出去后,福尔摩斯说:“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对于过去的事可以不深究。我处在私人地位,只希望正义得到伸张,没理由把所知道的事情泄露出去。谈到黑斯,等着他的只有绞刑架,我不愿拯救他。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公爵您可以使他明白,沉默对他是有好处的。从警方的观点看,他劫持这个孩子是为了得到您的赎金,要是警察他们找不到更多的问题,我没有理由将此事复杂化。然而我警告您,公爵,詹姆士·王尔德先生继续留在您的家中只会招致不幸。”
“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明白这一点儿。已经说好,他将永远离开我,去澳大利亚自己谋生。”“公爵,事情果真如此的话,我建议您和公爵夫人冰释前嫌。恢复你们之间的关系。您自己也曾说过,您婚后的不幸是由詹姆士直接造成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我也安排了,今天上午我给公爵夫人写了信。”
福尔摩斯先生站起身来说:“这样的话,我想我的朋友和我可以庆幸,我们在这里短短的停留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希望弄明白的还有一件小事。黑斯这家伙给马钉上了铁掌冒充牛的蹄迹,是不是从王尔德那里学来的这样不寻常的一招?”
公爵站在那里想了一会,露出一种十分吃惊的神情,然后打开一个屋门,把我们引进一间装饰得如博物馆一样的屋子里。他带我们走到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个玻璃柜,并且指给我们看上面的铭文:
此铁掌从霍尔得瑞斯府邸的护城壕中挖出。供马使用,但打成连趾形状使追赶者不能辨别方向,大概是中世纪霍尔得瑞斯经常出征的男爵的。
福尔摩斯打开了柜子盖,抚摸了一下铁掌,他的手指立刻潮湿了,皮肤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新泥土。他关上玻璃柜说:“谢谢您,这是我在英格兰北部看到的第二件最有意义的东西。”“那么第一件呢?”福尔摩斯折起他的支票,小心翼翼地放进笔记本。他珍惜地轻拍一下笔记本,接着说,“我是一个穷人。”然后把笔记本放进他内衣口袋里。
黑彼得
一八九五年是我的朋友福尔摩斯精神振奋、身体健壮的一年。他与日俱增的声望使他有无数的案件要办理,到我们贝克街来访的有不少著名人物。哪怕只是暗示一下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谁,我也会受到责备,被人认为不够慎重。正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为艺术而生存一样,福尔摩斯一直不因劳苦功高的成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只有霍尔得瑞斯公爵的案件除外。他是那样清高,也可以说是那样任性,如果当事人不值得他同情,那么,无论他怎样有钱有势,福尔摩斯也会断然拒绝他的。可是有时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却可以一连用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案情,但前提是案件离奇曲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和智谋。
这一年,我朋友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一系列怪诞奇异的案件当中。其中包括依照神圣教皇的特别指示对红衣主教托斯卡意外身亡案件的调查和臭名昭著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的捕获。紧随其后有乌德曼李庄园的惨案,这是有关彼得·加里船长之死的离奇故事。如果不记述一下这件离奇的案子,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就不够完善。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的朋友常常外出,而且时间较长,我知道他在办理一桩案件。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俗的人来访,并且询问巴斯尔上尉,这使我了解到我的朋友正用假名在某处工作。他有很多假名,以便隐瞒他的使人生畏的身份。他在伦敦各处至少有五个临时住所,在每个住所各使用不同的姓名和职业。可他在调查什么事情,却没有和我说,我对此也像平时一样不追问。可是看上去,他这回调查的案子是极其特殊的。早饭前他就出去了,当我坐下来吃饭时,他大步流星地回到屋内,戴着帽子,腋下夹着一根倒刺的伞状短矛。
我喊道:“天啊!福尔摩斯,难道你带着这个东西在伦敦四处走吗?”
“我去了一家肉店。”“肉店?”
“现在我胃口好极了。亲爱的华生,早饭前锻炼身体是很有意义的。但你一定猜不出我做了什么工作,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来。”“我并不想猜。”他一面为自己倒咖啡一面微笑着说:“如果你刚才到阿拉尔代斯肉店的后面,你会看到在天花板下挂着一头死猪晃来晃去,还有一位绅士穿着衬衣用这件武器奋力地戳它。这个很有力气的绅士就是我,我十分高兴没花多大力气就一下子把猪刺穿了,或许你也想试试?”
“绝对不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跟乌德曼李的离奇案件大概有点关系。啊,霍普金,我昨天晚上收到你的电报,一直盼望见到你。请一起吃早饭吧。”
我们这位刚进来的客人看上去十分机智,大概三十岁,素雅的花呢衣服掩饰不住常穿官方制服笔挺的派头。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莱·霍普金。他与福尔摩斯惺惺相惜,前者因后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侦破而对其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而福尔摩斯则认为他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霍普金面露愁容,带着十分沮丧的样子坐下来。“谢谢您,先生。来您这儿之前我已吃过早饭,我在市里过的夜。我昨天来汇报。”
“你汇报什么呢?”“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一点进展也没有吗?”“没有。”
“哎呀,我很想来侦查一下这个案件。”“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愿意您那样做,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可我却束手无策,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您帮一下吧。”
“好的,我仔细读过了目前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侦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怎样看那个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烟丝袋,那上面有线索吗?”霍普金好像吃了一惊。“那是他自己的烟丝袋,袋子里面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标志,海豹皮的,因为他本人是一个猎海豹的老手。”
“可是他没有烟斗吧?”“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的确很少抽烟,也许那烟是他为朋友准备的。”“或许有这种可能。我之所以提到烟丝袋,是因为我将接手这桩案子,我觉得最好将这个袋子作为调查的开始。我的朋友华生对此案毫无所知,至于我,再听一次事件的经过并无妨碍,所以请你给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主要情况。”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这是彼得·加里船长的一生简历。他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他善于捕海豹和鲸鱼。一八八三年他成为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他连续出航了数次,卓有成效。第二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年,他退休了。他旅行了几年,后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里斯特住宅区买下一小块地方,叫乌德曼李。他在这里住了六年,直到上周被害死。”
“这个人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日常生活中,他过的生活是严格的清教徒式,他个性沉默、抑郁,家里有妻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和两个女佣人。因为环境使人感到不愉快,甚至不能忍受,所以佣人常常更换。这个人经常喝醉,一喝醉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人们都知道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门,打得她们满园子跑,直到全村的人被尖叫声惊醒。”
“有一次,教区的牧师去他家里指责他行为不端,被他大骂,因而他被传讯。总之,福尔摩斯先生,要找到一个比他更蛮横无理的人可不太容易。海员们都叫他黑彼得,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的面孔以及大胡子是黑色的,而且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怕他的坏脾气。不用说,每个邻居都厌烦他且避而远之,他惨死后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表示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在那份调查报告中读到过,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也许您的这位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点。他在他家的外面造了一间木头小屋,他叫它‘小船舱’,离他家几百码,他每天晚上在那儿睡觉。这是一个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的小单间,他自己收拾被褥自己洗,自己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任何人都不准踏进他的门槛一步。屋子每面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一向紧闭。有一个窗户对着大路,每当夜幕降临,屋内灯亮起时,人们都好奇地望着这间木屋,并且猜想他在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调查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这间木屋的窗户所提供的几点情况。”
“您是否记得,在出事前两天,清晨一点钟的时候,有个叫斯雷特的石匠,从弗里斯特住宅区走过。当路过这个房子时,他停下脚步望了一眼窗户内散发出的光照在外面的几棵树上。石匠发誓说:‘从窗帘上清楚地看见一个人的头左右摆动,并且这个影子一定不是彼得·加里的,因为他很熟悉彼得。这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人的头像,但同那位船长的胡子不同的是,这个人胡须短而翘。’石匠是这样说的,他在小酒店呆了两个小时,酒店设在大路上,离木屋的窗户有一段距离。这是星期一的事,谋杀则是在星期三发生的。”
“星期二彼得喝得酩酊大醉后又闹了起来,暴躁得像一头吃人的猛兽。他在家附近逡巡,他的妻子和女儿听见他的动静便匆忙跑开了。晚上很晚,他才回到他的木屋。第二天清晨约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木屋的方向传来吓人的惨叫,因为他女儿总是开着窗户睡觉。他醉的时候时常大叫大吵,因此没有人留意他。一个女佣人在七点起来的时候,看到木屋的门开着,但是黑彼得过于让人害怕了,所以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门是开着的,看见屋里景象的人吓得面色全无,急忙往村里跑。很快我就赶到了现场。”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的意志是十分坚强的,但是我跟您说,当我把头探进这个木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成群的苍蝇、绿豆蝇嗡嗡叫个不停,地上和墙上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屠宰场。他把自己的木屋叫小船舱,的确,那像一间小船舱,呆在房间里如置身于船上。屋子的一头儿有一个床铺,一个贮物箱,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在一个架子上还有一排航海日志,完全像是我们在船长的舱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躺在木屋里墙的正中间,面孔因死时极为痛苦而痉挛着,他的胡子也痛苦地向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直透他宽阔的胸膛,又深插进后面木墙上,他像是一只被钉在硬纸盒上的甲虫,显而易见在发出那声痛苦的最后嚎叫后,他便死去了。”
“先生,我知道您在这时会怎么办,我也这样做了。我仔细地检查过屋外的地面以及屋内的地板以后,才允许移动东西,但没有发现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