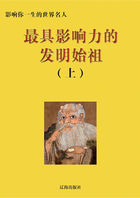在外交场合中久经考验的老练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对待客人时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与挑衅举止”感到“很吃惊”。在一次会谈中威吓麦克米伦后,赫鲁晓夫向特罗亚诺夫斯基吹嘘说,他曾“用电话筒戏弄了(这位英国首相)一下”,接着抱歉地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一定觉得很震惊吧。”
在他的“虚张声势”被识破后,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做出了让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儿子这么认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斗争,尽管他极力想让自己和他的手下人相信他取得了胜利。
外长会议于5月11日在日内瓦举行。同一天,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显露出欢快的语气:“首脑会晤即将举行。”麦克米伦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艾森豪威尔也“倾向于”这一想法,戴高乐同样如此。苏联的国际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然而,到了六月中旬,外长会议陷入了僵局。西方国家准备将柏林问题从他们的“一揽子方案”中剔除出来(仍然呼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改变他们在柏林的地位(通过减少驻军,就新的通道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但他们并不准备就基本权利做出让步,或是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苏联也许会接受一项临时性的协议,即在两个德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维持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但是葛罗米柯并不承诺如果协议达成后,这些权利能继续得以保持,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会谈进行当中,废止西方国家权利的威胁仍然存在。
甚至在5月11日前,艾森豪威尔已经明确表示,外长级会谈的进展是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他并没有具体界定这种进展指的是什么,但在日内瓦达成的结果肯定不属于这种进展之列。如果是这样,那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作出更好的表示呢?东德观察员被包括在日内瓦会谈之中(就他们与西德观察员就座的桌子形状进行了激烈而痛苦的争论),这已经是一种事实上的承认。此外,乌尔布里希认为外长会谈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尽管(他于3月告诉赫鲁晓夫说)德国问题的彻底解决会需要数年时间,也许甚至是数十年。急于想举行首脑会晤的是赫鲁晓夫,不是乌尔布里希。既然德国问题在一两年内无法得到全面解决,那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权利不会受到损害呢?
赫鲁晓夫也许有过这种想法。根据国务卿赫脱的看法,在6月7日之前,苏联的谈判立场好像都是灵活的,但到了6月7日,他们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为了达成一个新的德国条约,赫鲁晓夫威胁要建立一个新的柏林政权,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相反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没有退路的境地。不过,这一处境让人听起来觉得仍然是个机会。他于6月7日宣布国际形势没有陷入僵局。如果外长会议不能达成任何协议,那也许在首脑会晤上可以达成;如果外长会议失败的话,那首脑会晤就更有必要了。如果首脑会晤也不能取得进展,那“世界上的公众舆论”就会要求再进行另外一次尝试。“如果需要,”赫鲁晓夫在当月晚些时候慷慨地表示:“我很乐意与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不止一次的会晤。”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得应付与阿维雷尔·哈里曼的会谈,他们在6月23日进行了又一次马拉松式的交谈。此次会谈于下午一点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赫鲁晓夫穿着一件松垂的灰白色上衣,左胸前佩戴着两枚勋章,右胸上一枚,打着暗红色的圆点花领带,衬衫袖口上装饰着大大的红色链扣,哈里曼觉得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的会谈转移到了位于新奥加廖沃的贵宾别墅,在那里会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十点半。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还在门口站了15分钟,以确信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哈里曼有着富裕的贵族背景,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守势,将他现在的同事和以前的对手都包括了进来。“我是个矿工”,米高扬的父亲是个“水管工”,而科兹洛夫,“虽然不像我们这样粗俗”,原来曾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马林科夫“不值得一提——只不过是一只小鸡仔”,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说,贝利亚“也不值得一提”;只有莫洛托夫值得尊重。基里钦科现在好像是当然的接班人,但赫鲁晓夫提醒哈里曼不要把宝押在基里钦科的前途上。“我唯恐失掉我现在所拥有的特权,”赫鲁晓夫坦承地宣布:“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掌握着苏联共产党。如果想置我于死地,那你们只是痴心妄想。”
“在主席团里,你的话就是法律,是吗?”哈里曼问道。
“是的,”赫鲁晓夫回答道:“但没有一种法律是人不能设法规避的。”
赫鲁晓夫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也同样带有这种敏感。“不要认为苏联人还像沙皇将阿拉斯加卖给你们时那样穿着树皮做成的鞋子。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苏联“需要你们的友谊,但不是用软弱和屈膝换来的。如果你们想用实力和我们说话,那我们会作出同样的回答。”
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以守为攻。波恩只要一枚原子弹就“足够”了;三到五颗就可以解决法国、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生怕哈里曼还有什么疑虑,赫鲁晓夫比较了火箭有效载荷的不同规格:美国的导弹只能携载22磅重的弹头,而苏联的火箭可以携载2860磅重的弹头。
值得称赞的是,哈里曼对赫鲁晓夫的威胁进行了回击。赫鲁晓夫的威胁“听起来令人震惊”。他相信葛罗米柯先生在7月13日外长会议重新开始时会经得起考验。葛罗米柯将会反映苏联政府的观点,赫鲁晓夫严厉地说。如果不能,他就会被“解职”。之后,又是新的一轮威胁:西德“在10分钟”内就会被摧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波恩与鲁尔,德国就会完蛋。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伦敦是英国的中心。你们在我们周边部署了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火箭可以摧毁它们。如果你们挑起战争,那我们也许会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我们的火箭会自动发射出去”。
“你们也许可以告诉任何人你们的想法,”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承认阿登纳为德国的代表。他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阿登纳扯下他的裤子,从后面看你就可以知道德国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如果从前面看,你会看到德国是站不起来的。”
他后来又说道:“我们决心取消你们在西柏林的权利。在柏林驻扎着1.1万人的部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可以一口气将他们吞掉。……你们的将军们说要用坦克和大炮保卫你们在柏林的地位,但这些坦克大炮也是可以被烧毁的。”
如果将赫鲁晓夫言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写下来,看上去颇有希特勒的风格。不过根据哈里曼的叙述,这位苏联领导人“整个晚上都显得很亲切,脸上始终挂着笑容,频频举杯——主要是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他可以痛饮这种酒——不时奉承(哈里曼)是个了不起的资本家”。不过,他仍然进行着战争威胁。要是换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也许会担心美国采取过激的反应——斯大林就曾小心地避免使用这种恐吓手段,而这正是他的接班人的惯用手段——但是赫鲁晓夫知道(或者他认为自己知道),他可以将艾森豪威尔推到何种地步。
艾森豪威尔于7月8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已经有了关于赫鲁晓夫与哈里曼会谈的公开报道。在被问及他对赫鲁晓夫威胁的反应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冷静地回答道:“好,我根本没有考虑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应该沉湎于这样的事情,哪怕是模糊的最后通牒,或是威胁。这不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这种镇定自若是表面上的。事实上,随着赫鲁晓夫的举动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他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当麦克米伦呼吁举行高级别会谈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被迫参加首脑会晤”。但是“如果世界形势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他于4月7日对他的顾问们抱怨说,“未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除非我们能在谈判上取得一些进展(当时距离日内瓦会晤已经四年过去了)。”
艾森豪威尔捉摸不透与之打交道的人究竟是何种处事方式。“你们读过(赫鲁晓夫的)演讲稿吗?”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问道:“他在描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时用的那些词汇简直……”在被问及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麦克米伦访问期间的行为时,艾森豪威尔说这也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通过近距离观察作出评价判断的能力颇感自豪。在米高扬访问前夕,他希望他们能“努力透过彼此双方的面部表情,看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是否有着诚实与和平的动机?我们双方是否对军备竞赛所带来的负担感到力不从心,想找到一种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3月,他考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以“挽救局势”。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就下令国务院对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可能性进行一次“十分秘密的”研究。6月中旬,由于日内瓦会谈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私人秘书安·惠特曼说:“其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赫鲁晓夫先生到这里来,与总统单独会谈。”当外长会议于一个月后在日内瓦重新开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批准了邀请赫鲁晓夫前来美国的计划,他希望这一访问可以“打破外长会议中的僵局”。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将日内瓦会谈中的具体进展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前提条件。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负责向科兹洛夫转达这一前提条件,科兹洛夫当时正在纽约参加一个苏联艺术与技术展的开幕仪式,准备于7月13日搭乘飞机回国。本来墨菲应该转达的思想是,如果日内瓦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两国领导人可以在美国举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赫鲁晓夫愿意的话,会谈结束后还可以在美国游历一番。但是墨菲却说成是“没有限制条件的”邀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这一情况时,赫鲁晓夫已经于7月21日接受了这一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特别窘迫”,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他7月22日告诉墨菲说。现在他不得不经历一次他“拒绝”的会谈,他对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究竟想达成什么目的”都没有清晰的想法。
关于这一混乱状态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对此并不相信。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颇感吃惊。几个月来,他一直想得到这样的邀请,但没有成功。他在7月份告诉一个美国地方官员代表团说,他随时可以去美国访问,也希望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到苏联来。但是直到那时,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并因此感到“十分伤心”。
当科兹洛夫于一个周末的早上从纽约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位于莫斯科河边的别墅里,突然科兹洛夫打来电话,并马上驱车赶了过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希望设法得到美国的邀请——至少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或是为了那种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特别紧张。但是现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意味着什么?是某种转机吗?”
赫鲁晓夫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充满了巨大的满足感”。他儿子记得:“我甚至可以说,是欣喜万分。他将此看成是美国已经最终承认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成为苏联第一位受到正式邀请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这好像就是赫鲁晓夫一直期待的“突破”,即“在柏林问题上他在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下取得了具体成果”。
不出所料,当外长会议于7月13日重新开始时,他们之间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直到8月份才宣布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但与华盛顿在日内瓦的交锋才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尼克松副总统在7月23日至8月2日对苏联的访问预示着两国间即将到来的高层交往。
两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赫鲁晓夫开朗热情,尼克松拘谨克制。不过,两人对细微之事都特别敏感,都坚定地显示出自己不能受到羞辱。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尼克松脑子里考虑的是“在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过程中,我应如何表现”。虽然想到了可能会受到赫鲁晓夫的威逼,但他并不愿意“以威胁对威胁,以吹嘘对吹嘘”。不过,他“还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会谈是一场激烈的口角战。几天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受控国决议》,谴责苏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控制。这种决议是美国国会的例行做法,从1950年开始每年都有,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一决议好像旨在软化他的立场,以配合尼克松的访问。
“这种决议令人作呕,”他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与尼克松会谈时说:“就像新鲜的马粪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难闻的了。”下面就是尼克松当时回答的原话:“我觉得主席先生搞错了。还有比马粪更难闻的东西,就是猪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