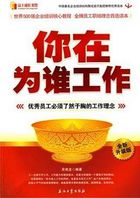他已经不是在中国科学院的他了。他从1962年到1965年在鞍山图书馆,年年被评为馆里的先进工作者。有一年还评卜全市的先进工作者。他本来是目录员,很轻省的。但他要求去当辛苦的采购员。馆里自然同意。只不过馆里不会想到,他当采购员可不是专拣重担挑。他只有利用采购图书的机会,才能到各地图书馆去收集在鞍山不会有的资料。钢都鞍山只有钢铁。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地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了这个刻苦又穷酸、谦卑又韧长的体重八十斤的嗜书者——马蹄疾。他的探亲假也用来跑上海的图书馆。没钱住旅馆,所以天热偏往南方跑,可以夜宿火车站,冻不着。这天有人把他推醒。他睁开眼来,一时不明白这是在哪儿?他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仰望一位俯视自己的严肃的民警。他是谁?马蹄疾懵懵懂懂的。他是谁?民警也在想。民警已经多次注意到这个一把就可以拎起来的瘦人干,天天晚上蜷缩在上海火车站。倒是不像小偷。可他为什么像个流浪汉?马蹄疾如实招来。民警破例照顾——招待他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大模大样地睡一夜。
马蹄疾少不了还要找到一些大学者家里去查资料。极拘束的、怯怯的,所以敲门极轻,轻得人家听不见。然而又非“打入”这些学者教授的私人藏书室不可。“笃”、“笃”、“笃”、“笃”敲来,敲木鱼似的,念佛朝圣似的。也许,对学术的虔诚,确使他超然于现世的苦痛肮脏之上。当他终于得以走进私人藏书室,面对他一路餐风露宿特来朝拜的着作时,他风尘仆仆而心无纤尘!
于是,三十五万字的《<水浒》书录》和三十五万字的《<水浒>资料汇编》完成了。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马蹄疾,真正先进的是他的业余工作,自留地活儿。
一个不被现实接受也无法接受现实的陈宗棠逝去了。一个别人挑不出毛病、自己也能把公活私活都做好的马蹄疾,稳扎稳打地站住了,如果没有“文革”的话。
“文革”,他到底还是被挑出了很多毛病,譬如,资产阶级杂家,黑笔杆。
1970年他被分配到鞍山的一个水泥厂当磨机工。当初他在图书馆时还能来个巧干,要求当图书采购员。如今经历了隔离审查和干校劳动的犯人生涯之后能回鞍山当个工人,能够天天回到他的家,能够下了班就不用再惧怕什么人,除此之外,他再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他只能更多地向自身索取。他的家,是一间容纳了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岳父共五个人的号称九平米实质只有六平米的屋子。他搭了一个三层的铺。岳父、妻子和小儿子睡下铺,大儿子睡中铺,他睡上铺。他上床时只能把身子与床平行着插进屋顶和床板之间的空隙。实在没有写书的地方。于是他天天去拣砖。拣那不过三分之一块的碎砖。
拣一点,砌一截墙。终于接出——向两平方米的小房,是比着他自个的身高盖的。倒像要给他自己做只砖砌的套子。如果来个比他高一厘米的客人。就得弓身而入。好在本来就不考虑接待客人。此乃马蹄疾的书斋。不过,屋顶只一层油毡纸。夏天,屋里气温高达三十五度。屋外杂草乱石的,蚊子太多。越是夏天,越得关紧窗子,活活像用“砖套”做汽锅清蒸马蹄疾。
越是压抑自己就越向自我榨取。外表的越来越缩小,内心的越来越扩大。马蹄疾在两平方米里像洗桑拿浴似的蒸腾着大汗,却又像做瑜珈似的坐得住。他不挑剔这两平米的“砖套”;“砖套”也不会挑他的毛病。他接受这两平米,他爱这两平米,连同它的全部缺陷。只有在这两平米里,他再不用去应酬,去敷衍,去看人眼色,去唯唯诺诺,去接受欺侮,去劳动改造,去赎罪!不,他在这个空间里做的不仅仅是他最想做的,而且是非他莫属的事,他才能得到对自我的肯定和确认。
他发了一千多封信给全国各地三十几家图书馆,查了上千种书,抄录了上万张卡片。譬如鲁迅书信,鲁迅一生发过多少信?
现在能找到的有多少?都在哪儿?和鲁迅通信的,一个个人是干什么的?当时鲁迅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写的是什么事?看来鲁迅共发过约五千六百封信,能找到的大约一千三百封。由那上万张卡片写成六十万字的《鲁迅书信系年考》,然后方有十二万字的《鲁迅书信札记》。
表面的极其软弱掩护了——而不是掩盖了——内心的极其坚韧,或用鲁迅的话说叫:韧长。到70年代末,北京中华书局要出版他在60年代前期完成的《水浒》资料汇编)了。此时他在鞍山群众艺术馆工作。出版社要他三天后把三十五万字的清样校对出来好立即付印。艺术馆恰恰要派十几个人到鞍山郊区去调查农村文化工作,也是为了逐级上报,做给上级看的。农民知道艺术馆的人要下来检查,临时花个上千元买上一堆书摆好了,等艺术馆的人一走,就把书分了。
据说这叫“小共产党‘糊弄’大共产党。”本来,干这件事多一个少一个马蹄疾,都无不可。有同事为马蹄疾这三十五万字着急,提出代他去。不行,就是得马蹄疾去。这几近是一种惩治,一种对于别人都没写书就你写出书来的惩治。
同事为马蹄疾愤愤然。马蹄疾却精神勃勃了:“我很高兴。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
他的“轮胎说”使他鼓胀起来几乎觉得天下没有难得倒他的事。他坐上闷罐子似的长途车,赶一百来里土路的黄沙坨06月天气,别人在这样汗气袭人的颠颠车里苦不堪言,独独马蹄疾觉得很好,他可以睡觉了。车颠得不能看书,他可以当仁不让地睡了,受之无愧地睡了,不睡白不睡了。不用花钱买“床位”,不用怕民警注意他,不用动脑子,不用干这干那,可以一路睡去。人生难得这样消停!
到了黄沙坨,头一天调查,写完报告——明知无用的报告,然后就校对清样。农屋只有一盏二十支光的灯,还黄红黄红的。清样上全是繁体字,且学术着作一点误差出不得的。然而马蹄疾已具有了越苦越发奋的自我调节机制。三十五万繁体字,就在这二十支光的“彩灯”下,如期校完。马蹄疾提起笔在书末写上“1980年6月10日凌晨于黄沙坨。”
不过说起这件事,他是兴奋的,为他的“轮胎说”的伟大胜利而兴奋。
1980年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式把马蹄疾从鞍山调去。现在,他可以专一做他想做的事了。这是他自己的时间,这是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用的。好比包产到户后农民有责任田,就要计算着想密植想间种想一年收两茬想从责任田里无尽无休的收获。他的家还在鞍山。文学研究所每星期五上班。他就得清晨三点半起床,四点离家,赶五点十分的火车,七点半到沈阳,再坐公共汽车,八点半到社科院。这本来也没什么,如果上班的确老有事的话,如果人人都得星期五上班的话。但所里有人两周才来一次,因为上班常常也没有事。偏偏马蹄疾就得每周五准时来,否则就是纪律问题。规规矩矩地上下班,实在心痛这来来徊回路上的时间和上班闲扯的时间。“来上班也没有事!”他发牢骚了。如果这是当年在水泥厂,或是在鞍山图书馆,他是不会讲这种牢骚话的。他早已失却了讲牢骚话的功能。现在,他如同一个昏睡二三十年的人,给扎了针灸。他的做人的功能正在恢复。他有了做人的意识——不光是做学问,而是做人。比如,他会发牢骚了,虽然只发了那么一点点。
他的发牢骚的功能立刻受到了社会的检验:院里批评他骄傲了,目中无人了。不发给他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表。而比他上班少的人倒发到了表,更不用说学术成果的多少了。
1981年,在文学所的全所会上,马蹄疾突然激愤地站了起来,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和他一贯的谦卑恭顺反差太大,于他不啻是在“政变”。加上他说话越激愤,就越本色,绍兴口音越人风味就越突出,大家一时听不清他之乎者也地说什么。这两句话鲁迅曾四次引用过,认为这于绍兴人是很有光彩的。当然绍兴人马蹄疾在文学所的会上用,譬喻不当。他无非想讲你们背后说我,我是不怕的!有问题为什么不摆在明面上来?为什么别人发了申报助研的表,而偏不发给我?
绍兴人马蹄疾的“报仇雪耻”随着他发言的结束而结束了。秀才造反,没有不失败的。他本来正在和院里一位同志合作写一部书。他“雪耻”之后,有关方面叫他交出全部他收藏的有关这部书的资料,改为集体创作。而马蹄疾,等于成了资料员。
马蹄疾同意了。
他不是在“报仇雪耻之国”长大的越人吗?是的。不过他历经几十年的异化程序,早已是一个怕扣上个人奋斗的帽子、怕得罪头头的当代闰土了。鲁迅的《故乡》中的成年闰土见到儿时的密友,竟是喊过儿子:“水生,给老爷叩头。”明明人家不是老爷,不愿作老爷。所以有闰土就会有老爷,就会有各种“四老爷”。
马蹄疾老老实实地把他积蓄的四五十斤两大捆资料从鞍山背到沈阳,又拉上一位党员干部一起去出版社。他怕他一个人去的话,出什么事也说不清。如今拉来一位党员人证,并由“人证”对出版社说,马蹄疾承担不了这本书的写作,所以要改成集体创作了。
话由别人说,这话的效果不管怎么样,单位里有关方面总不会怪罪于他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他自己都讲不清?刚刚建立起来的做人的意识,动摇了,崩溃了。秀才造反之后怎么比造反之前还孱弱,还不堪一击?
出版社说,如果这本书改成集体创作,那么,本社取消这个选题。
出版社交给马蹄疾一封信,让捎给原先和马蹄疾合作的那位同志。捎信?好的。给捎走了。信中说马蹄疾的写作可以,希望那位同志的文章也按马蹄疾的写法稍改一下。
把这样一封信亲手递给收信人,不是等于对人家说,我行,你不行吗?
马蹄疾从此又有了新的怕。怕人家误以为是他在出版社搞的鬼,丢了人家的面子,怕人家和他过不去。人家是领导。国人的常规思维方式是:得罪了领导在单位里就不得翻身了。
其实人家可能就没把这事放心上。但是马蹄疾开始了他的“赎罪生涯”。他人前人后地想和这位收信人亲善友好,大事小事和人家讲,尊重人家的意见。这个学会那个学会提名人家当会长,说人家贡献怎么怎么大。人家在不在场,听没听见,马蹄疾不管。马蹄疾的感觉是一直有个很大很大的他。对于马蹄疾,他是无所不在的。
马蹄疾还有不少事都得靠他。譬如,妻子还在鞍山,还没能调来沈阳。马蹄疾在社科院还没分到房子。还要评职称。
后来,1987年,马蹄疾终于登门到他家里:你为我的职称,费了很多心,非常感谢你。现在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又要靠你了,这事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他点头了。没有他的点头,马蹄疾的妻子能在1987年10月调来吗?
2.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
1966年,胡风在狱中曾抄录他1957年写的两首《拟出狱志感》。其二为: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马蹄疾从此又有了新的怕。怕人家误以为是他在出版社搞的鬼,丢了人家的面子,怕人家和他过不去。人家是领导。国人的常规思维方式是:得罪了领导在单位里就不得翻身了。
其实人家可能就没把这事放心上。但是马蹄疾开始了他的“赎罪生涯”。他人前人后地想和这位收信人亲善友好,大事小事和人家讲,尊重人家的意见。这个学会那个学会提名人家当会长,说人家贡献怎么怎么大。人家在不在场,听没听见,马蹄疾不管。马蹄疾的感觉是一直有个很大很大的他。对于马蹄疾,他是无所不在的。
马蹄疾还有不少事都得靠他。譬如,妻子还在鞍山,还没能调来沈阳。马蹄疾在社科院还没分到房子。还要评职称。
后来,1987年,马蹄疾终于登门到他家里:你为我的职称,费了很多心,非常感谢你。现在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又要靠你了,这事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他点头了。没有他的点头,马蹄疾的妻子能在1987年10月调来吗?
3.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
1966年,胡风在狱中曾抄录他1957年写的两首《拟出狱志感》。其二为: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桶底幸存三斗米,墙头重挂万年旗。
远离奖苑休回首,学种番茄当写诗。
负荷尚堪糊数,晴穿破衲雨蓑衣。
马蹄疾的《<水浒>书录》后记,题为《一部献给妻子的书》。因为1968年他被关进学习班的那天,妻手薛贵岚对他说:“《<水浒>书录》是你十多年的心血,造反派要这本书稿,你就一切向我身上推,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当晚,她即把书稿转移到一个工人成分的亲戚家中。第三天十多名造反派押着马蹄疾到家搜“黑材料”。马蹄疾说早由妻处理掉了。造反派即去妻的单位,说不交出书稿,即以包庇反革命论处。妻说:只许你们造老马的反,不许我革老马的命吗?老马的东西,早叫我一把火给烧了。
他们1966年结婚的时候,马蹄疾三十三元工资,薛贵岚二十七元工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因为马蹄疾尊崇中国的脊梁鲁迅,所以给儿子取名叫陈鲁(读者不会忘记马蹄疾本姓陈)。
这位鲁鲁瘦得只有脊梁没有肉。贵岚抱着这根“脊梁”只是哭,哭得奶水都回去了,只好给孩子订牛奶,开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