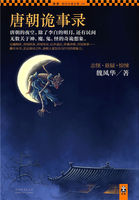护士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留下布罗德卡一个人无所适从地呆在病房。他头昏脑涨,没有办法清醒地思考问题。他一个劲地想,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布罗德卡竟然被关进疯人院!他喟然长叹,尔后竟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这时候护士又回到病房。她凛冽的目光逼视着他,递给他一杯水和两颗粉红色的药片。
布罗德卡接过药片放在掌心,在护士严厉地注视下,他做出吞下药片的动作,暗中将药片滑进罩衫的袖口里,这一连串动作他想都未想,只是条件反射般的这样做了。
这些药片,脸色突然缓和下来的护士说,会把他心里的“坏念头”——她就是这样表述的——去除掉。
布罗德卡又是一个人。老天啊,他心里想,你竟然昏睡六天。
找不到他的手表,布罗德卡没有了时间概念,他感到无以复加的孤立无援。
他就这样躺在床上苦思冥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听到钥匙在房门转动的声音,进来的仍是那名护士。她面无表情,拿开床底下便盆的盖子,朝里面瞟了一眼。布罗德卡根本没留意到床下有这么个便盆,更别提用了,他恶心得反胃。
和来时一样,护士一言不发出了病房,没一会儿功夫返回来,她端来餐盘,上面有个小汤罐,闻上去像是肉汁,布罗德卡觉得自己饿了。
他赔着小心问护士,他何时能够见到医生。护士的反应很烦躁,痛斥他怎么这么多事,并说,知道这些他还为时过早。光是听到她的这种腔调,布罗德卡就打消了继续发问的想法,并使他找机会逃跑的念头更加坚定。
饥肠辘辘的布罗德卡在护士的监督下舀起肉汤,味道无比恶劣,不过就算是他最爱吃的菜肴在这种凶巴巴的目光注视下他也品不出什么滋味。在他最终把肉汤喝光之后,护士把餐盘端走,离开病房。
病房里只剩下布罗德卡孤零零一个,望着四壁白墙,他无法不胡思乱想,心中充满着惶恐和愁闷。朱丽埃特为什么还没打来电话?他依稀记得,在警察把他押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对他说:“别怕,有我在你身边。”还有一个白大褂说:“他不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杀妓女的家伙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任何记忆。
后来的时间布罗德卡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窗站立慢慢地消磨。
他的体力已经恢复,思维日渐清晰,用脑思考时也不会那么容易疲倦。他把尿撒在床底下的便盆,往里面扔进本该吞下的两枚药片,看着它们一点点溶化。
朱丽埃特在他昏睡的这六天里没有打过电话吗,他问自己,她把你这个大家谈论的“杀妓女的家伙”,在教堂大发癔症而被诊定为精神错乱的病人丢弃在精神病院不管不顾了吗?他的这种忧虑愈发严重。恍惚中他好像看见朱丽埃特在和别的男人耳鬓厮磨。他悲不自胜地双手紧紧攥着床单,大声咒骂,忽听到从走廊传过来的脚步声,又陡然闭上嘴巴。
门开了,住院医师走进来,他身材瘦高,鼻梁上架副镍边眼镜。他温和地对布罗德卡说,他不必太过担心,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让他尽快痊愈。医师还问他感觉如何。
他觉得很好,布罗德卡回答,又补充一句说,他很高兴终于有人能和他谈谈他所谓的病情。
医师只是点头,然后轻轻敲了敲布罗德卡的脑袋,检查他的眼睛。最后他问布罗德卡,他的家族中是否有谁患过神经方面的疾病。
布罗德卡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向医师保证,他绝对不属于该被关起来的病人,还有他什么时候能出院。
住院医师听到这一问题的反应几乎和护士一样的生气,他断然回答,布罗德卡根本用不着惦计出院,像他这样的病人必须要封闭治疗。
布罗德卡又想解释大教堂里的事端是如何引起的,可没等他开口,医师已经转身出了病房。
下午稍晚时分护士端着晚餐走进来,餐盘上是汤、面包干和茶,仍有两个粉红色药片。布罗德卡又一次动作麻利地解决了药片,然后无滋无味地喝起汤来。
是夜,他躺在床上,思索着如何将自己的逃跑计划付诸实施。
经观察他发现,中午前后会有辆货车开进内院,运走装满脏衣物的箱子。如果他能进到箱子里躲在衣物下面,就可以随车逃到外面重获自由。
第二天早上护士进来送饭,布罗德卡细细察看她的一举一动,病房的钥匙就挂在她围裙的裙带上。
中饭时间她再次走了进来。就在她把餐盘往小桌子上搁的一刹那,布罗德卡猛向前一扑,把护士撞倒在床,他抢走钥匙,在护士还没有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之前,他已经蹿出病房,将门反锁。他听到护士在屋里喊救命的叫声,还有用拳头砸门的动静。
长长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双开门挡住布罗德卡的去路,多半上了锁,于是他往相反的方向跑至楼梯间。
他的运气真是不好。
楼梯间里住院医师张开胳膊堵在他面前,那架势似乎早已等候在这里。随后两三个护工赶到,将布罗德卡押回病房。
病房里脸涨得通红的护士在等着,她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就好像他是加害于她的魔鬼。她快速整理好衣服,用怨毒的眼神盯了盯她的病人,离开了房间。
这之后,一名粗壮的护工替代女护士照管布罗德卡,论强力对抗,他绝不是那个壮汉的对手。
“布罗德卡先生?布罗德卡先生,您有访客。”
半睡眠状态的布罗德卡一下子惊醒。
“访客?”他迷迷糊糊地问,“谁呀?”
护工嘻嘻笑着递给他一件白色浴衣和拖鞋,“是个极为漂亮的女士。”他说。
朱丽埃特,布罗德卡激动地冲口说道,上帝啊,您终于让她来啦!
会客室位于二楼的一扇磨砂玻璃门后面。布罗德卡在护工的陪同下走了进去,早已等在里面的朱丽埃特从椅子上站起来,扑进他怀里,搂住他的脖子。朱丽埃特头发散发出的香味如同给布罗德卡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刻意回避这几天挨口子的艰辛,颇有些不自然地对朱丽埃特说:“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听到这话朱丽埃特更感难过,这段时间她心力交瘁,每天望着镜中的自己,内心的倦怠早已在脸上留下清楚的痕迹。
“我过得还凑合,布罗德卡。”朱丽埃特没有说真话,她也不打算把警方怀疑她涉嫌艺术品造假案这件事告诉给他。
两人坐在屋中央的小桌子旁,布罗德卡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我还以为你不再理我了呢,我不怪你。”
“我为什么要这样?”朱丽埃特反问,她把手搭在他伸直的胳膊上。
“嗯,”布罗德卡臊眉搭眼地说,“谁愿意管一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家伙,一个疯子,自称看到他早已过世的母亲。”
朱丽埃特生气地说:“你知道我爱你,布罗德卡,你不该胡思乱想,这对你没有好处,只会让你的处境更为艰难。你同我乃至对面的那个护工一样正常,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布罗德卡耷拉下脑袋,他低垂着目光对朱丽埃特用很低的声音说:“上次,在斯特凡大教堂……我那么确定,那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这期间我想明白了,是我过于绷紧的神经让我的大脑出现幻觉。过去那段时间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难道这就是把我关在这里的理由?”
朱丽埃特握着布罗德卡的手,直视他的双眼,然后她话音很轻但是坚决有力地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显然也跟你犯了同样的错误,老实说,我也看见了那个女人,虽然我不认识你的母亲,不过我找到这个……”
她去够她的手提包。在一旁默默听着他们对话的护工探长脖子,唯恐错过什么。朱丽埃特注意到他的关切,就主动把敞开口的手提包朝他伸过去,好让他瞧见里面有什么。护工不由得难为情。
“对不起。”说着他把视线转向窗外。
朱丽埃特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搁在布罗德卡面前的桌上。
“这张相片是从你的相册里找出来的。”
布罗德卡睁大眼睛看着照片,朱丽埃特完全想象得到他的心里正想些什么。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在教堂里表现得那么疯狂了吧?”布罗德卡小声地说。
朱丽埃特点点头,“我虽然从没见过你母亲,但是照片上的这个女人看起来和我们在大教堂里面碰上的那位老妇人完全一样,甚至穿着打扮的风格都是如此相同,同样鲜艳扎眼的花格外套。”
布罗德卡默不作声。朱丽埃特看到他的嘴唇在微微颤动,他的双手紧紧按在桌面上,好像不敢碰触照片似的。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子,布罗德卡,”沉吟片刻,朱丽埃特说道,“你没有失心疯。你不要问我这一切做何解释。照我来看,或者这两个人本身就是无比相像,或者大教堂里的那个女人确实是你的母亲,某个人导演了这个故事,其目的是为了毁掉你……”
布罗德卡默默地点着头。他脑子里乱极了,各种想法纷纭杂乱,形势突然间起了变化,他成了一起密谋的牺牲品。他该如何向那些关他的人讲清楚这件事呢?
他一定要从这里出去!
他偷眼瞅瞅那边的护工,看他能否听到他们的谈话,然后他近乎耳语地问朱丽埃特,她知不知道院方打算把他关多久。
她耸了耸肩算是回答,安慰他说,她会请最好的律师和病理鉴定专家,把他从这里救出去,等一会儿她会跟住院医师谈谈。
布罗德卡朝她凑过来,轻轻地说:“我受够了,再这样关着不超过三天我准得发疯,快把我弄出去,否则真的要崩溃了。你身上带钱了吗?”
“带了,”朱丽埃特很诧异,“你要多少?”
“一万先令,多一点儿更好。”布罗德卡悄悄说道。
朱丽埃特没再多问他在这个封闭的精神病院要这么多钱做何用。她在桌子下面打开提包,将几张折起来的钞票交给布罗德卡。
趁护工没注意,他把钞票塞进浴衣兜里。
布罗德卡刚藏好钱,护工用钥匙敲打着窗台石板,大着嗓门叫道:“会客时间结束!”
布罗德卡和朱丽埃特长久地热烈拥吻,作别时他听到朱丽埃特对他说“我们会好起来的!”他低着头被护工看管着从原路返回病房。
布罗德卡把经过的每一处都一一记在心里。
瘦高个的住院医师名叫皂鲁斯,是十足的讨厌鬼。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古怪,他却自认为很有个性。人们能够原谅他的怪癖——他老是控制不住地眨眼睛,或者总是用拇指和食指拽耳垂——多是因为他长年来尽跟行为失常的人打交道。朱丽埃特进了他的诊疗接待室还没有落座,他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就粘住她,将她从头到脚贪婪地细细打量一番,就好像他多年没见过女人似的。
朱丽埃特真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干脆走掉,但她还是改变了主意。如果她想让布罗德卡尽快从这里出去的话,她需要这个男人的帮忙。
这个房间和大多数医生的接待室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屋子里有一张写字桌、一个玻璃柜、一把椅子和一张察看病人病情用的蒙上塑料布的平板床。房间里的空气污浊,弥漫着说不出来的一股味道,这气味朱丽埃特以前从未闻到过,酸酸的又略带些微辣。铁栅栏窗已经足够让人心慌发冷,门上没有把手,而是种特殊按钮,更让朱丽埃特隐隐不安起来。
“您姓考林,为什么您丈夫姓布罗德卡?”医师问。
“我们还没有结婚,”朱丽埃特实话实说,接下来却是谎话,“但是我们像夫妻一样生活好多年了,布罗德卡先生没有别的亲属。”皂鲁斯用右手擦着左手手背,没有正眼看朱丽埃特,“那么原则上说您并不算家属,我没有权利告诉您有关病人的任何情况,请您谅解……”
朱丽埃特跳起来,双手撑在写字台上俯身怒视着皂鲁斯镜片后面的眼睛,“您听着,医生,”她气汹汹地说,“您对我的家庭状况作何评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我到这里来就是想要知道,您打算什么时候让布罗德卡先生出院,没有理由让他继续留在这儿!”
皂鲁斯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以此来躲避朱丽埃特咄咄逼人的目光,“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您,布罗德卡先生患的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不能够正常地思维和进行情绪表达,迫切需要治疗,而且得留院察看。得这种病的人他的首要症状就是时刻觉得有人要攻击他。您或许还不知道吧,布罗德卡先生曾经袭击过一名护士。
我现在也只能做到用强制手段阻止他的无法自控的暴力行为。”
朱丽埃特又坐回到椅子上。布罗德卡一一精神分裂?她使劲摇晃着脑袋,皂鲁斯不禁奇怪地看着她。随后她用平静的语气说道:“如果布罗德卡得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话,您也可以把我立即关起来,因为我们两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场面。”
“你们看到了什么?”医师故作感兴趣地发问。
朱丽埃特打开手提包,拿出照片伸到皂鲁斯眼前,“我们在斯特凡大教堂看到一位老妇人,和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一模一样。”
“即便如此,”医师说,“这也不能是大闹教堂的理由。难道此人威胁布罗德卡先生?”
“不是那样子,”朱丽埃特不动声色地回答,“根本不可能,这个人是布罗德卡的母亲,而她在两个月之前去世,据说葬在慕尼黑的森林公墓。我想知道,如果您碰上这种事情,您会作何反应。”
皂鲁斯审视着面前的朱丽埃特,镜片后面的双眼闪现出凶光。
他现在会说什么,朱丽埃特心想,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皂鲁斯的回答简短,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他只是说“哦,这样啊”。
“是呀,就这样啊!”朱丽埃特以嘲讽的口吻重复一遍,她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她接着问道,语气中充满叱责:“您打算把布罗德卡先生扣留到几时?”
皂鲁斯两手抱胸,“怎么是扣留呢,布罗德卡先生呆在这里是出于治病需要。至于还得治疗多久,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像这种偏执狂患者绝不允许一两天就出院的。我向您保证,我们将竭尽所能让他早日康复。”
“可布罗德卡没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