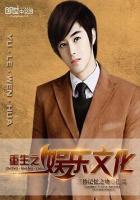我走了过去,吴雅有些慌张地装着打电话,我站在她身后半天,她才转过来,看到我好像吓了一跳,捂着胸口道:“吓死我了,你干什么。”
那个假啊,到底是模特,太不专业。
“你干什么?”我问道。
我知道吴雅跟给徐晴不太对付,我真怕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她捣什么乱,影响了徐晴开业的大好心情。
吴雅咬了咬嘴唇道:“算了,说实话吧。我听说她俩弄了个店,我琢磨这么多年姐妹了,想送个红包,又怕她们不收。”
“真的?你那么好心?”
“我到底有多坏啊,你很了解我么?哼。”
吴雅真是漂亮啊,又嫩又美,嗔怒之下,眉毛一皱,看得我心这个蹦。
“走吧,都来了,进去看看呗。”我说道。
“不了,不了,你帮我把红包递过去吧。”吴雅道,说完递给我个红包,包好了,上面写着“生意兴隆”。
我接了过来,问道:“进去坐坐吧。”
吴雅摇了摇头。
我有些无奈地拿着红包回到了店里。
“给。”
“谁给的啊。”徐晴有些奇怪。
“你绝对猜不到。”
“快点说,忙死了。”徐晴说。
“吴雅。想不到吧。”
一旁赵舒冷冷道:“她有那份心?”
“我也很奇怪啊,不过来的都是客,我让她进来坐坐,她不进来。”
赵舒道:“她倒是也得敢,我看她就来气。”
徐晴那面拍了赵舒的手一下道:“干啥啊,这么多年,即便你再看不上她,她也是咱们姐妹。而且能有这份心,就行。有啥过不去的。”
我一旁帮腔道:“就是,我看她也挺可怜的。”
“人呢?”徐晴问。
“我让她来,她不来。好像还没走,我感觉她可能有事。”我耸了耸肩。
徐晴走出了店,应该是看到了吴雅,小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几乎是连拖带拉地把吴雅弄进了屋。
找了一个包间,把玛丽叫了下来,玛丽看到吴雅也是一愣,随即笑道:“我随便说声,还以为你不能来呢。”
吴雅笑了笑道:“这不是来了。”
“今天都别走,晚上我们四姐妹不醉不休。”徐晴宣布道。
真忙啊,这一天,从早到晚,八点还有不少人,不过徐晴把店交给了侍应生,拉着我们到一旁的火锅店吃火锅去了。
这天吃火锅还真有点热了,但是没办法,炒菜吃着吃着就凉了,还是火锅好,越吃越热乎,而且我发现好像女生都比较喜欢吃火锅,尤其是麻辣火锅。
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吃清汤的,我觉得这样能吃出肉味来。
但是,今天我不是主角,人家带着我是为了让我当司机,把几个人都送回去。
所以我很识相地闭嘴,然后看着她们在一起杯来酒往,喝得不亦说乎。而我捧着豆浆,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
徐晴和赵舒真的是很高兴,这毕竟是她们的产业,而且局面这么好,连我也感到兴奋。
这四人里面,吴雅跟她们的关系都不好,但是玛丽除外,玛丽与她们三人的关系是另一种关系,所以玛丽不停地讲着笑话,打着圆场。
避免让气氛尴尬。
几杯酒下肚,几个美女满面红光,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引得四周食客不停地扫向这桌,我能感受到目光里蕴含的妒忌,那些目光杀人般地瞄向我,让我无比受用。
吴雅站起来倒了一杯酒,自己一饮而尽说:“这第一杯酒,我祝姐姐们生意兴隆,日进斗金。”说完又倒了一杯酒,再次一饮而尽道:“第二杯酒,小妹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恳请姐姐们的原谅。”然后又倒了一杯酒,还打算喝,一旁的徐晴急忙拉住吴雅的手说:“有事啊,说吧。”
吴雅摇了摇头,喝了那杯酒道:“第三杯酒,以后小妹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不会……”没说完,捂着嘴跑向了卫生间。
赵舒冷冷地说道:“天天就知道整事。”
徐晴瞪了赵舒一眼问道:“玛丽,老五怎么了?”
玛丽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啊,我也是好久没联系她了。”
赵舒继续冷冰冰地说:“精神病呗。”
“你行了啊,干什么啊。”徐晴道。
赵舒不再说话,拿起啤酒干了下去。
玛丽道:“我过去看看吧。”
话没说完,那面吴雅已经回来了,眼睛通红,面色苍白,显然已经吐过。
见吴雅坐下,徐晴举杯道:“刚才你敬我们,我们还没喝呢,来,干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说了,以后我们还是好姐妹。”
玛丽举起了杯,一旁的赵舒抱着肩膀,一动不动。
“雪糕,你干什么。”徐晴问道。
赵舒冷哼了一声说:“先问明白她想干啥,不然你让她卖了都不知道。”
声音中透出的冰冷与恨,让我不寒而栗。
这就是我一直害怕的,赵舒一直以来透出的那种恨意。
我曾经跟徐晴说过,我感到赵舒的眼神中总带着一种恨,无论看谁都是。
徐晴笑我神经过敏。
但是现在,赵舒在吴雅面前,把这种恨意毫无保留地展露了出来,我的冷汗立刻就下来了。
我也曾经怀疑我是不是神经过敏,但是赵舒这个表现让我非常确定我的直觉,她看徐晴的目光中,真的带有一种恨,与她看吴雅的恨一样,只多不少。
吴雅干了手中的酒,徐晴和玛丽也跟着喝了下去,赵舒犹豫了一下,举起杯放在唇边意思了一下,没有都喝。
吴雅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这都是我自己作的。但是我跟你们这的不一样。你们是家养的,我是野生的,有的时候我不得不为了一口饭去拼命。”
吴雅瞪着通红的眼,看着火锅上升起的白气,轻描淡写地诉说了她不堪回首的过去。
讲述如此悲惨的过去,如同讲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一般。
我的亲生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远走他乡,仅仅是因为我母亲给他生了四个女儿。
我母亲坚持了三年,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将我们扔在了年老的奶奶的门口,自己改嫁走了。
一年后,奶奶死了,临死也没有再见到我的父亲,甚至不知道我父亲是死是活。
然后我就由十四岁的姐姐养活。
那一年我四岁。
姐姐十六岁的时候跟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远走他乡,也不管我们了。
那一年我六岁。
村里来了杂技团,我被二姐以二百块钱给卖了,二姐跟我说:“妹,你走吧,走还有一条活路。”
我从那以后,就不知道我的姐姐们是死是活了。
于是我开始练起了杂技,坐着团长的破篷车,开始游走天下。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很漂亮,很多像我这种遭遇的孩子早就被打成了残疾,然后去乞讨。
但是我又是不幸的,也因为我漂亮,我十四岁就被团长到处送人,为了让到各地演出更顺利一些。
黑社会,官员,甚至仅仅是场地所有者。
你不知道他用我做了多少交易。
十六岁那年,我偷了两千块钱,跑了。
那个时候我去哪里都不知道,跑到火车站买了一趟下一班的火车就走了,然后就到了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