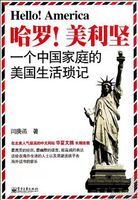第十六卷 (2)
“幸福的土人!啊!我怎么就不能享受永远陪伴你们的和平生活!我四处飘泊,浪迹天涯,一无所获。而你们,安静地坐在橡树下,听凭日月流逝,你们知足常乐,你们比我聪明,像个孩子似的,满足于睡眠和玩乐。即使有时乐极生悲,你们也懂得排遣悲怀,仰望上苍,动情地寻求我不知名的神秘之力,它会怜悯可怜的野蛮人。”
讲到这里,勒内的声音又消失了,年轻人的脑袋垂到胸口。夏克塔斯在暗影中伸出手臂,抓住儿子的胳膊,以感动的声调对他喊:“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阿梅里的兄弟听到这声呼唤,回过神,为自己心绪的紊乱脸红,请父亲原谅他。
年老的野人说:“我年轻的朋友啊,像你这样的人,心潮难免波动不平,只是你要克制这种性格,它已给你造成那么多的不幸。你在生活中比别人更易感受痛苦,这不奇怪,高贵的人比卑贱的人要忍受更多的痛苦。继续讲述你的故事吧,你刚才已使我们游历了欧洲的部分地区,让我们了解你的祖国吧。你知道我见过法兰西,你知道我与它有哪些亲密的联系,这使我眷恋它。我爱听你谈谈那个伟大的一国之主指路易十四。,他已不在人世,我曾参观他的华美的窝棚。我的孩子,我只靠回忆生活了,喜欢回忆往事的老人,犹如林中的衰老的橡树,它已无绿叶点缀,但有时,缠在它的残枝断桠的外来植物会盖住它光秃的躯干。”
阿梅里的兄弟听了这些话,安静下来,他继续披露心事:
唉,我的父亲,我无法与你谈论那个伟大的时代,童年时我只见过它的末期。待我回国时, 它已不复存在。民众出现旷古未有的令人震惊的突然变化,原本人才辈出,崇敬宗教,风尚严肃,突然变得观念动摇,大逆不道,道德败坏, 世风日下。
我本希望甩掉纠缠着我的不安和强烈的欲望,但一切都落了空,探讨人生方面,我一无所得,却又丧失了我天真无邪的快乐。
我姐姐的行为也令我不解,她似乎乐于增添我的烦恼。我到达巴黎前的几天,她却离开了巴黎。我写信给她,说我打算去找她,她赶紧给我回信,劝我放弃这计划,借口说她有事要办,还不知要去哪儿。对着这样的“友谊”,人在时不冷不热,人走茶凉,有难不能同当,有福不能共享,我怎能不生无穷的伤感!
不久我便发觉,在祖国比在异域更孤单。我一度曾想进入我不喜欢, 也不了解我的社会。我的那颗从未有过激情的心,寻求着能拴住它的人,但我发现自己给予他人的要比他人给予我的多。别人并不要求我有深挚的感情,有教养的谈吐。我只好贬低我的生活以迎合社会。我到处被人视为浪漫,我为自己扮演的角色羞耻,越来越愤世嫉俗,并打定主意到远郊隐居。
开始时,我对默默无闻、独立不羁的生活还饶有趣味,我隐姓埋名,混入芸芸众生之中,混入辽阔的荒原之中。
我常坐在一座人们不常去的教堂里,好几个小时陷入沉思。我看见可怜的妇人匍伏在上帝面前,看见犯罪的人跪在忏悔台前,离开时一个个脸色和霁。外面低沉的嘈杂声就如激情的狂泛,人世的风暴到了神殿便安静下来。上帝啊,你见过我在这些神圣的隐蔽所里流泪哭泣,你知道我曾多少次跪在你的足下,恳求你卸去我生存的重负,或求你改变我暮气沉沉、老气横秋的面貌!啊!谁没有偶尔产生过更新的需要,在急流中返老还童,希望灵魂在生命之泉中新生?谁不会偶尔因堕落而消沉,再鼓不起劲去从事伟大、高尚、正义的事业?
暮色降临,取道回隐居所,我停住脚步,站在桥上观看落日。夕阳染红暮霭,如同世纪这一巨钟的钟摆,在金色的霞光中缓缓摆动。然后,夜伴我回家,穿过迷宫般偏僻的街巷。看着万家灯火,我仿佛置身于灯火下悲欢离合的场面。我想到,在如此多的屋檐下,竟没有一人是我的知己。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哥特式教堂的钟楼,响起报时的钟声,远远近近的教堂响着不同音调的钟声,钟声不止不歇。唉!在世间,每一个小时增添一座坟墓,每一个小时有人流泪。
开始我还神往这种生活,但日久便生厌倦。我讨厌这单一的情景,讨厌同一的念头。我探究我的心,自问我到底要追求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要追求什么,只是我认为林木可以怡情悦性,我决计结束刚开始的生活,似乎它已吞噬了我几个世纪的时间。我要到乡间去。
我兴致勃勃地为这计划做准备,对每一项计划我的态度都如是。从前启程去周游世界,为了住进茅屋我也匆匆动身。
有人责备我爱好不定,幻想多变;责备我被想象折磨,急于得到欢乐,人们指责我好高骛远。唉,我只不过出于本能,去寻找我未尝过的幸福而已。我觉得我到处受到限制,我觉得过去的事毫无价值,难道这也是我的错?然而我却喜欢生活中单调的感情,如果我还痴痴地相信幸福,我就要在习惯中寻找它。
绝对的孤独,大自然的景色,不久使我陷入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境界。我无亲无故,茕茕孑立,形单影只。我无恋人,被过剩的活力折磨。有时,我会不期然地脸红,激情如岩熔,小溪般在心中奔流;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高叫。夜里,不管是醒着还是做梦,我都心烦意乱。我无法填补生活的空虚,我下到谷底,攀至山巅,使足力气呼唤未来理想的爱人。我迎风拥抱她,仿佛在江河的呜咽中听到了她的声音。一切,天上的星辰,甚至宇宙中生命的本原,都是这想象的虚幻。
然而,这种平静而骚乱、贫乏又丰富的状况也非毫无魅力。一天,我为消遣,到溪边采撷一枝柳枝,在每一片随流水逝去的叶子上寄托一缕情思。生怕被突发的革命夺去王冠的国王,不会有我这样强烈的忧愁不安,而我,柳枝上少去一片叶子,我也要忧愁。啊,人是怎样的脆弱啊!永不衰老的人多么天真!我们崇高的理想竟会降到何等稚气的地步!还真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像我的柳叶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上面!
怎样表达我在闲游时这一堆转瞬即逝的感觉?激情在一颗孤独而空虚的心中所引起的回响,犹如在沉寂旷野中风与流水的低语,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游移不定中,秋天不期而至。我狂喜地进入这暴风雨的季节。我时而想当一名与风、云、幽灵搏斗的武士,时而羡慕牧人的生活,他们在林中的一角点燃荆棘,用篝火暖手。我倾听他唱的忧伤的歌曲,这些歌使人感慨:任何国家,真情流露的歌都是悲歌,即使它表达幸福时亦然。我们的心好比残缺不全的乐器,断弦的竖琴,我们不得不用哀叹的乐调演奏欢乐的音符。
白天,我迷失在与树林相接的大片灌木丛里。些许的物件都勾起我的遐思梦想!在我面前飘落的枯叶,炊烟在树梢袅袅上升的窝棚,橡树干上被朔风吹得抖颤的苔藓,离群的岩石,枯萎的灯心草、簌簌作响的水潭,远处狭谷里孤独的钟楼,常常吸引我的视线。我目送头顶上飞过的过路的鸟群。我想象它们要去栖息的地方的气候,无名的河岸,我真想趴在它们的羽翼上飞翔。潜在的本能折磨我,我觉得我自己也只是个旅客。不过,来自天上的声音似乎对我说:“人啊,你迁徙的季节尚未到来,等冥风刮起,你就可以展翅飞向你仰慕的无名之地。”
“快来吧,渴慕已久的暴风雨,你们该把勒内带往另一个世界!”我这样疾呼,迈开大步走着,脸庞发烧,风在我的发间呼啸,我感觉不到雨滴和雾粒,我欣喜、焦躁,像被我心中的魔鬼操纵。
夜晚,朔风摇撼我的茅屋,倾盆大雨直泻我的屋顶,我隔窗凝望天上的月,它像破浪的白舟划破层层乌云,我心中似更添活力,我似有能力创造新的世界。啊!要是有一个人能与我一起体验这激情该多好啊!噢,上帝!如果你能赐我如意的妻子,要是你能像给亚当一个夏娃,你也给我一个由我身上分出去的妻子……,天仙似的美人啊!我会拜倒在你的脚下,把你拥在怀里,我会恳求上帝为你献出我的余生。
唉!我孤独,形单影只!颓丧攫住我的躯体。从童年起就有的厌世感又以新的力量回到心头。很快我的心再不给我的思想提供食粮,只有那理不清的烦乱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听我倾诉的上帝的教士啊,请你原谅一个几乎被上天夺去理智的不幸的人,我心怀宗教的信仰,但思考时却如不信教的人。我的心爱着上帝,而我的思想却不接受它。我的举止、言论、感情与思想矛盾重重,阴郁虚假。然而,难道人总很清楚他之所思,能肯定自己的考虑?
一切都离我而去:友谊,世界,退隐。我尝试过各种生活,但它们只给我带来不幸。社会排挤我。阿梅里抛弃我。失去了清静,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清静是我惟一能得救的最后一块跳板,而现在这块跳板却正在沉入深渊!
我决计摆脱生命的重负,便很有理性地投入这荒诞的行动。我从容不迫,我没确定离开人间的日子,我要细细品尝人生最后时刻的滋味,效法先人,尽力体会灵魂升天的感觉。
我认为我必须安排我的财产,只好给阿梅里写了信,我对她的遗忘流露了几句怨言,也许我透露了逐渐涌上心头的感动,我却自以为我的秘密掩藏得很好呢。我的姐姐早已了解我的内心,毫不费力就猜到了我的秘密。我信中的口气很不自然,问起过去我从不关心的事,她警觉了,她没有复信,而是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要真正体会我后来的创巨痛深,乍见阿梅里时我的激动,你们就明白她是我世上惟一的亲人。我全部的感情,童年时代的甜蜜回忆都与她有关。见到她时我欣喜若狂,我已经很久未见一个了解我的人,一个我能向她披露心曲的人了!
阿梅里扑入我的怀抱,对我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啊,你想寻死,姐姐却生存着!你怀疑她的心!你别解释,别辩解了,我什么都知道,都理解,就如天天与你在一起。你想骗我?骗我这个连你最初的感情都了如指掌的人?我知道你的坏脾气,厌世,不公正。在我搂着你的时候,你发誓吧,发誓今后再不自寻短见,再不发痴了。”
阿梅里讲这番话时,她看着我,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温存,她在我的额上印满了亲吻。她像慈母,比慈母更温存。唉!我心里又溢满了欢乐,像个孩子,我只求得到安慰。我让步了,她要求我郑重其事地起誓,我毫不犹豫地照办,没想到日后我会不幸。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沉浸在相处的喜悦里。早晨,我不再孤零零一人,我听见姐姐的声音,我因快乐幸福而战栗。阿梅里气质高贵,外表与灵魂一样优雅纯洁,她性情温柔,举止娴雅,神气带些许的迷惘。她的心,她的思想,她的嗓音和谐协调,哀婉动人。她具有女性的羞怯腼腆、慈爱,具有天使的纯洁优美。
补偿我的轻率的时候来临了。为了能受苦,我在胡言乱语中渴望遭受不幸,这可怕的愿望啊,上帝在盛怒之下让我如愿以偿了。
啊,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泄露什么啊!你们瞧我眼中涌出来的泪水。我甚至会……,几天前,你们休想从我口里掏出这秘密……,现在,一切都完了!
不过,老人们啊,让这件事儿永远埋藏在沉默之中吧:要记得它是在荒原的树底下讲出来的。
冬天快结束,我发现阿梅里失去了休息和健康,而她使我得到了休息和健康。她消瘦了,双目深陷,步履软弱无力,语无伦次。有一天,我撞见她泪流满面,跪在十字架下。喧嚣的俗世,荒僻的山野,我在家或不在家,白日还是黑夜,一切都使她心烦意乱。禁不住的叹息来到唇边又咽了下去。她时而不知疲倦地长途跋涉,时而步履维艰。她拿起活计旋即又放下,打开书却又读不下去,欲语又止,突然痛哭流涕,又退出去祈祷。
我试图揭开她的秘密,我询问她,把她搂在怀里,她微笑着答话,说她和我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三个月就这样过去,她的情况一天坏似一天。我发觉她的落泪与她的神秘的书信有关。每当她收到信,要么比平日安静,要么更激动。一天早晨,她没来与我共进早餐,我上楼到她的房间,我敲门,没人应我。我轻轻打开房门,里面亦无人。我在壁炉上看见有个写着我的地址的小包。我哆嗦着抓起包裹,将它打开,读到下面一封信,我一直将它保存到今天,为了今后不再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