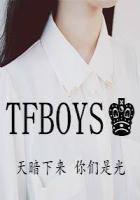青木很惊讶,不过也就仅仅是惊讶而已。对于这位公爷的举动,他已经懒得再浪费力气去思考了。先是教自己武功,然后教着教着就哭了,哭了还不让说,结果弄得自己差点死掉,等快咽气的时候,又把自己救回来,还说当自己挨揍的时候他之所以不出手,是因为害怕贾文正结果了自己。
等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活过来,武功却又不教了。明明是一个武夫,非要教自己读圣人之言,可是圣人之言才学了一半都不到,又莫名其妙改成了教兵法。空口白话地说了一个晚上,自己愣是什么东西没听懂,这位公爷却不生气,还说是他的错。这些乱七八糟的解释,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位公爷又说要给自己赎身。
青木无所谓了,再接下来,就算李牧之要认自己做孙子,青木也不觉得自己会有多惊讶了。
单膝半跪在不远处的贾文正,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李牧之,陷入微微的沉思。在他看来,李牧之这个举动,实在有些此地无银的味道。
他对青木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惜才的程度,天底下的人才多了去了,却从不见这位神将对谁如此上心过。当年姬荣登位之前,被誉为赵国有史以来最上佳的储君人选,可姬荣想拜李牧之为师,李牧之却直接说了句“殿下万尊之躯,无需学这些搏命之术”,拒绝得干脆至极。
那么青木,他到底和李牧之是什么关系呢?
贾文正眯起眼盯着青木脸颊上的刺青,心里越发困惑。早在好几天前,他就亲自去问过青木的监工,据那个监工所说,青木确实是在他家里待了整整十年时间。可是堂堂镇国公,怎么可能让嫡亲血脉流落民间,当了整整十年的奴隶?
正苦思其中关节,陡然间,贾文正只觉周身一冷,体内的气息抑制不住地乱窜起来。
他强行将气息压下,然后找到了这股无双霸气的来源。
廉将军抽出腰间宝刀,好似无视李牧之的存在,上前一步,抬起手,刀锋直面青木,冷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扑面的刀气,让青木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李牧之大喝一声,将这股刀气逼退,单手贴住青木的后背,输入一股真气,怒声喝骂道:“廉负荆,休要以为老夫奈何不了你!你再敢放肆,老夫宁可赵国从此无良将!”
黄紫貂脸色阴沉,轻咳一声,阻止廉负荆道:“廉将军,区区小事,犯不着动刀动枪,王上命我二人来,只为传旨。”
廉负荆盯着李牧之半天,挥刀入鞘。宝刀入鞘的霎那,几乎所有跪在大门口的监工们,全都瘫软了下去。
青木喘过气来,有些不可思议地看了廉负荆一眼,相比起李牧之轻轻三指敲断砚台的惊艳,廉负荆这以意杀人的本事,更是显得震撼人心。
“谁是这位小哥的监工,出来吧!”
黄紫貂一声吩咐,青木的主人郑大连忙从人群的后方爬出来,跪在地上,颤声道:“回……回大人,小的就是青木的监工。”
黄紫貂道:“卖身契可在身上?”
“在……在!”郑大哆嗦着脱下外套,从里面撕下一个缝死的布袋,打开后,拿出厚厚一叠二十个奴隶的卖身契,满头大汗地翻了半天,总算找到青木的。
李牧之接过卖身契后,看了一眼,就随手撕掉,道:“过些日子,赎款会从邯郸寄给你。”
郑大忙磕头道:“青木能跟着公爷,是他的福气,小人不敢收公爷的钱,就当……就当送给公爷吧……”
“放肆!”李牧之怒吼一声,“老夫焉用你一个小小的监工送礼?”
郑大吓得磕头如捣蒜,哭腔道:“公爷息怒,公爷息怒,小人嘴贱,小人……自己掌嘴!”说完,就把脸拍得啪啪作响。
李牧之不耐烦地喝退郑大,然后又问黄紫貂道:“黄公公此行前来,身边可带着珍珠之品?”
黄紫貂道:“王上赐给镇国公的礼物中,有上好东珠十颗。”
李牧之道:“先拿给老夫用用。”
黄紫貂微笑道:“镇国公尚未接旨,咱家怎好将王上的赏赐给国公爷?”
“黄公公不给,老夫就不接旨。”
李牧之这话说得实在不要脸,黄紫貂愣了愣,继而微微一笑,对身边的一个侍从道:“给镇国公将王上的赏赐拿来。”
侍从匆匆跑上车,将车里的东西往外拿。
几个内饰官托举着木盘接住,没一会儿,十个人拿着盛满金银、珍珠、布匹的盘子,在李牧之跟前站成一排。
黄紫貂对李牧之道:“王上念镇国公戴罪在此地监察清苦,特命咱家送来黄金百两、上等东珠十颗、龙虎丹一壶、鼋皮护身软甲一件、名剑破军一把,还有上等佳酿一坛。”
李牧之走上前,别的不看,拿起一颗东珠,轻轻一捏,圆润光滑的东珠,眨眼成了齑粉。
“此处可有医士?”
李牧之一声问,立马有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躬身道:“小人是。”
李牧之伸手一指青木,吩咐道:“将他脸上的刺青印痕刮掉!”
那医士一下子就明白了李牧之的意思,忙道:“公爷,小人观这位小哥脸上的刺青印痕,少说也至少有十年的,便是重新挖开,用这上等东珠粉敷脸,也不见得能消除啊!”
“废什么话!让你干你就干!”
在众人的注视下,医士用刀划开了青木的脸颊,青木疼得直吸冷气,却是站着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挖完,李牧之就把东珠粉末一股脑地敷在了青木的脸上。手下还剩下一点,随手一挥,当尘土撒掉。
医士看得心里直摇头,又忍不住提点道:“公爷,既然是敷了,那便请做得细致一些。依小人看,多敷几次总比只敷一次强,在这位小哥脸上结巴之前,须每日都以这东珠粉敷脸才好。”
“有理!”
李牧之拿起装龙虎丹的葫芦,打开来将里面的药丸全都倒掉,接着将剩下的九颗东珠一一拍成粉末,装进葫芦里,将葫芦口封好后,递给青木,吩咐道:“孩子,听到刚才医士说的了吧?这东西,要一直敷到脸上结巴为止。”
青木显得很庄重地接过沉甸甸的葫芦,点了点头。
黄紫貂眯起眼,问道:“镇国公,现在可以接旨了吧?”
李牧之没有理会他,继续对青木道:“孩子,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奴隶,不可在以奴才自称了,知道吗?”
“我知道了。”
“好!”李牧之满意地笑笑,又说,“从今往后,不能再给别人下跪磕头了,知道吗?”
“知道了。”
“老夫教给你的武功,要每日修习,知道吗?”
“知道了。”
李牧之伸出手,慈爱地摸了摸青木的头,转过身,对黄紫貂道:“黄公公,随老夫去城门口,老夫要望着秦地接王上的旨意!”
黄紫貂点点头,转身进了马车。
车队起驾,慢慢朝正泰安城正西门去。
跪在大宅院门口的众人,等车队走远,才一一站起身来。
贾文正拍拍膝盖的土,回想起刚才李牧之问青木的话,觉得有些刺耳,他微微自嘲着笑笑,看到正一动不动目送李牧之的青木,走上前去,仿佛随口问道:“青木,你去郑大人家之前,是住在哪里的?”
青木转头见是贾文正,傻傻一笑,却是站直了回答:“回大人,小人生在邯郸。”
“邯郸?”
贾文正眼睛一亮,不知何意地拍了拍青木的肩头,然后沉默着朝院子里走去。